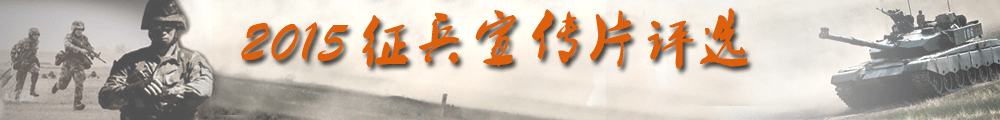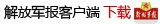飞行是那一代年轻人最强烈的梦想
1921年,康姆亚迪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祖上是农民,他在普通的中学读书、毕业,“唯一特殊的,这里是美国最早出现航空工业及相关产业的地方”。
1903年12月,莱特兄弟驾驶“飞行者1号”开始了人类第一次有动力飞行,这次摇摇晃晃的飞行历时12秒,飞行距离36米。康姆亚迪出生的时候,航空业也还只是一个18岁的“毛头小伙”。
康姆亚迪3岁的时候,美国陆军的两架飞机历时176天,着陆57次完成第一次环球飞行,飞行员的名字家喻户晓,是当时最耀眼的明星。“当我变成个小伙子,飞行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最强烈的梦想。”
康姆亚迪的父亲是一名飞机发动机工程师,也是他飞行的启蒙教练,“爸爸引导我成为一个航空爱好者,飞行是最时髦的事情。在飞的过程中,有种自由和控制的力量。如果你骑过单车,就能对那种感觉有一点感受。”
17岁的康姆亚迪考取了飞行执照,他的理想是在20岁时做一名私人飞行员。对飞行的热爱,是那些飞虎队、驼峰飞行员在年轻时共同的特点。
飞虎队的二十名王牌飞行员之一——迪克•罗西在回忆录中写道:“年轻时,我有一位是航空迷的朋友。有一次我们到了火努鲁鲁,我的朋友告诉他要下船逛一逛,岛上有一个机场,大家可以乘小飞机绕岛一圈。我们坐飞机,绕岛一圈,从空中鸟瞰这个美丽的小岛。返回时,开飞机的说,感觉如何?我说和坐公共汽车差不多,不就是坐在那里逛逛嘛。开飞机的说,愿不愿意来点刺激的?我说,行啊。他说,好,交五块钱,我们把你带上。他们有一架大湖式双座教练机,露天座舱。我就和他一块儿上了飞机,飞行员飞了所有的特技飞行动作。我那时候想:这才叫飞行呐。我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发现我迷上了飞行。”
迪克•罗西后来被海军航空部队录取。在中缅印战场上,迪克•罗西拥有飞虎队中击落敌机6.25架的记录,并创造了飞越驼峰航线750次的最高纪录。
1939年欧战爆发,美国开始备战,大量生产飞机,并招训飞行员。康姆亚迪没有看到海军的征兵广告,也不知道退役后可以拿1500美元,因为他报名参加了陆军。当时,空军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种,隶属于陆军或海军。
“是战争让我有机会进入到这个很昂贵,并且科学性很强的行业。我的命运就这样和战争联系上了。”多年后,垂垂老矣的康姆亚迪这样说道。
美军运输机载物资飞越喜马拉雅山。
不管天气多恶劣,飞机夜以继日地飞行
1941年,康姆亚迪在美国南部的加州高级飞行员培训学校开始接受飞行训练。
加州明亮的阳光给从美国北部来的康姆亚迪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里一整年都是好天气,每天都可以飞,所以在学校的每一天我都没闲着”。刚学飞行的“菜鸟”经过训练,成了合格的飞行员,“一年后,我通过中、高级考试”。毕业后的康姆亚迪在澳大利亚和北非战场上飞了一年运输机,一天接到调防指令,指令夸了一通他表现优异后,在末尾告诉他,他将被派到印度战场,给驻扎在中国的部队运送物资。
1941年11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三个多月后,中印开辟驼峰航线。半年后,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继桂越公路、滇越铁路后也被日军切断,驼峰航线便成为维系中国抗战的唯一国际通道。
一开始,驼峰空运很不理想。1942年的全年运输量只有4732吨战略物资,不仅低于中方的要求,也低于美方每月运输物资500吨的承诺。
据史迪威将军测算,经驼峰运输5000吨物资的必备条件是:304架飞机,275名机组人员,3400名地勤人员,空运线两端各有5座机场,每座机场能够容纳50架运输机。此外,还要储备大量的航空汽油和飞机零部件,建设复杂的导航装置和空袭警报系统,部署足够的保护航线的空军力量。所有这些,都成为制约空运的不利因素。
1943年中国在昆明、桂林、柳州、云南驿四处扩建机场,又在宜宾、呈贡、羊街、陆良等地修建了十几座机场。美国也明显加强了驼峰空运的力量。空运指挥官汤姆斯•哈丁上任以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从此,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不管有多少从缅甸起飞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拦截,500多架C-46、C-54、C-87型运输机夜以继日地飞行在这条危险的航线上。
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中国云南怒江东岸和印度,中国军队也向日本人发起反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姆亚迪接到了他的调防指令。
对驼峰航线康姆亚迪早有耳闻,他关系最好的两个飞行学校的同学,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坠毁的。“我们都希望找个安全点的工作,所以离开的那天,兄弟们为我开了一个送行会,他们安慰我:‘伙计,其实哪都不安全,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