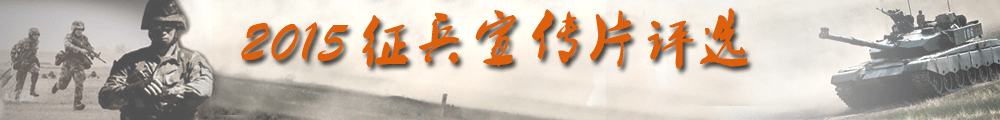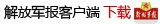“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
刚进入6月,位于中缅滇藏接合部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已比其他州县更为闷热。只是在州府泸水县城随意走走,汗水便可湿透衣衫。但驾车向泸水县片马镇行去,绕着高黎贡山的悬崖陡壁和密林行驶,不断失去高度又重新攀爬的一路,温度陡降。
在一处白杜鹃盛开之处,“风雪垭口”一下子出现在视野里。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口,卷起掺杂着雨水的风,裹着不知是山雾还是云涛的灰白色,笼在不远处还遗留的日军碉堡之上。
18年前的此时,亦是吴子丹去世后的第七年,当年的美国飞行员汉克斯跟随一队人正是从这里行往一处山脊,找到了吴子丹牵挂半生的那一架53号。
53号是这条航线上所有失事的飞机中,少有的被亲眼目睹并及时测定坠落方位的。据不完全统计,这条航线自开辟到结束的1300多个日夜里,像53号那样坠落损毁的空运飞机超过600架,牺牲的机组人员和乘客超过1500人。
至今,还有不知数目的飞机残骸和机组成员长眠于从印度汀江到云南昆明的山谷、丛林,无数个家庭的丈夫、父亲、儿子、兄弟,从一处出发就再没有返航,这便是抗日战争中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驼峰航线”。
“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当年的飞行员们对“驼峰航线”如此描述。
“驼峰航线”并非一条线路,主要可以分为约800公里的南线与约1150公里的北线:南线过怒山、澜沧江、横断山脉,到达大理,经云南驿直达昆明;北线经缅甸葡萄、丽江程海,再到昆明。
日军占领缅甸密支那之后,配备了大量“零式”歼击机,当地的机场、通讯、导航和警报等飞行保障设施全部为日军所用。东条英机曾指示日本驻缅防空部队,最大任务就是切断中印空运路线。
为了躲避日本战机,夜间航行较远的北线成为“驼峰航线”空运不得不做的选择。然而,当时的飞机动力有限,没办法完全飞过山顶,经常要在海拔4500-5500米上下的“峰背”之间航行。更要命的是,“驼峰航线”位于欧亚大陆三大强气流团的交汇点,“鬼天气”是很多“驼峰”飞行员常见的噩梦——
“我们在黄色的浓雾中从印度起飞,季风雨洒在挡风玻璃上,成了数支急流。在12000英尺(约3658米)高空,雨变成了雪。我们看不见翅尖……我们开始缓慢下降,我们什么都看不见,窗户从里边冻得严严实实。”
“我们在16000英尺(约4877米)高空遇到了强冷空气前锋。整个机身突然开始震动,螺旋桨上结冰了,我们除不掉冰……我们遇上了暖气流,棍子似的螺旋桨松了,掉下了冰的大块块……飞机在昆明着陆,因为机身连同两个螺旋桨坏了……我们运的货物是炸药,又是一个正常的日子。”
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天气使得从阿萨姆到昆明的飞行多数时间只能依靠仪表。飞行员桑德曼曾总结自己的“驼峰”经历:“我在中缅印战场飞了706小时5分钟,75%的时间是仪表飞行或者夜航,或者两者兼有。”
虽然天气是“驼峰航线”的第一大“杀手”,但是美国空运指挥官哈丁上任颁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即便是被美军租用的商用航空中国航空公司,因为天气而停航的情况也被降到最低。
当时,每月空运的战争物资达44000吨,1945年7月最高为71000吨。驼峰空运的总飞行时间达510万小时,云南的昆明、陆良、呈贡、云南驿、沾益和四川的宜宾、新津、彭山、广汉、泸州和重庆等机场在最繁忙的时候,每75秒就有一架飞机从机场起飞。
飞机坠毁了,便补充;人员牺牲了,就再聘。从1942年日本占领缅甸,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打通的约三年时间里,驼峰航线便是盟军物资运入中国的唯一通道。这是中美两国政府必须不惜代价确保的“一线生机”。
1945年1月6日至7日凌晨,从非洲和印度来的浓密的锢囚峰面一路攒积力量,在孟加拉湾遇上湿气,在“驼峰”上空形成了每小时100-125英里(约161-201公里)的风,随之而来的是湍流、结冰、积云,还有高尔夫球大小的冰雹和漫天狂风。而在天气预报到达之前,“驼峰”上的运输机便已经出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像极了今天的灾难片:
一架C-46运输机的副驾驶嘴里没点着的烟斗掉出来,飞到了天花板上;飞行员唐尼记得,从看不见的飞机不断传来“呼救”和“再见”的声音;报务员福特带着降落伞,打开机舱门把大量货物扔出机舱,身体有一半悬在空中……
那一夜之后,据传损失多达50-60架飞机。事故研究者奎因的数字是:18架飞机和42名机组人员和乘客。
那一夜之后,开辟两年半的载客夜航在驼峰航线取消了,管理官员在天气最坏的时候终于有权取消航班。
彼时,距离日本无条件投降,只有7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