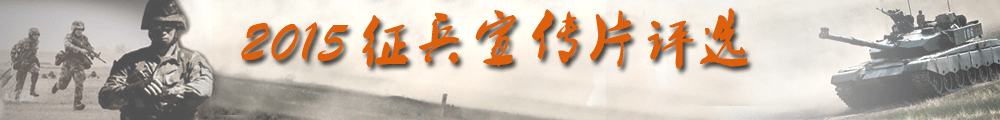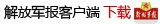不管天气多恶劣,飞机夜以继日地飞行
1941年,康姆亚迪在美国南部的加州高级飞行员培训学校开始接受飞行训练。
加州明亮的阳光给从美国北部来的康姆亚迪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那里一整年都是好天气,每天都可以飞,所以在学校的每一天我都没闲着”。刚学飞行的“菜鸟”经过训练,成了合格的飞行员,“一年后,我通过中、高级考试”。毕业后的康姆亚迪在澳大利亚和北非战场上飞了一年运输机,一天接到调防指令,指令夸了一通他表现优异后,在末尾告诉他,他将被派到印度战场,给驻扎在中国的部队运送物资。
1941年11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三个多月后,中印开辟驼峰航线。半年后,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继桂越公路、滇越铁路后也被日军切断,驼峰航线便成为维系中国抗战的唯一国际通道。
一开始,驼峰空运很不理想。1942年的全年运输量只有4732吨战略物资,不仅低于中方的要求,也低于美方每月运输物资500吨的承诺。
据史迪威将军测算,经驼峰运输5000吨物资的必备条件是:304架飞机,275名机组人员,3400名地勤人员,空运线两端各有5座机场,每座机场能够容纳50架运输机。此外,还要储备大量的航空汽油和飞机零部件,建设复杂的导航装置和空袭警报系统,部署足够的保护航线的空军力量。所有这些,都成为制约空运的不利因素。
1943年中国在昆明、桂林、柳州、云南驿四处扩建机场,又在宜宾、呈贡、羊街、陆良等地修建了十几座机场。美国也明显加强了驼峰空运的力量。空运指挥官汤姆斯•哈丁上任以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从此,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不管有多少从缅甸起飞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拦截,500多架C-46、C-54、C-87型运输机夜以继日地飞行在这条危险的航线上。
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在中国云南怒江东岸和印度,中国军队也向日本人发起反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姆亚迪接到了他的调防指令。
对驼峰航线康姆亚迪早有耳闻,他关系最好的两个飞行学校的同学,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坠毁的。“我们都希望找个安全点的工作,所以离开的那天,兄弟们为我开了一个送行会,他们安慰我:‘伙计,其实哪都不安全,哪都一样。’”
飞越这种地方,绝对没有人再相信无神论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最著名的刊物《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1943年3月11日,24岁的美国飞行员詹姆斯•福克斯与中国飞行员谭宣、王国梁驾驶一架飞机满载物资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飞往印度汀江。一个多小时后,53号飞机在飞越云南高黎贡山时与地面失去联系。
1996年6月的一天,一位中国猎人在云南高黎贡山片马垭口发现一堆铁皮和许多他从没见过的仪器。经过探察,这就是当年的53号运输机。
尽管美军在驼峰航线上配置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飞机,但是狂暴的天气和日军的战斗机,一直是驼峰飞行员难以摆脱的梦魇。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萨尔温江、怒江直达我国的云南和四川。这条航线途经的地区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比比皆是。当时一般的运输机爬高限度不及7000米,只好在高山峡缝中小心翼翼地曲折穿行。机翼下这些起伏的高山,被形象地称之为驼峰。
“这种地方,绝对没有无神论的人。每个人在起飞前都在心中祷告。” 康姆亚迪说,“每次起飞前都希望这次飞行更容易,但实际上每次都能学到新东西。”
被分配到驼峰航线后,没有人告诉康姆亚迪应该注意些什么,他就匆匆忙忙开始了第一次飞行。“第一次飞,我当副驾驶。飞机加满油,货舱里也装满了炸弹。我坐在驾驶座里,正驾驶突然对我说,你应该把安全带系到最紧。这就是我飞驼峰前得到的唯一特殊培训。”
二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美国靠三个工具赢得了这场战争--登陆艇、C-47运输机和越野车。C-47是美国的新型运输机,1940年开始装备部队。“它的名字是信天翁,但我看来,粗粗短短的机身使它看上去像一名敦厚的老实人。
即使今天驾驶C-47飞驼峰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