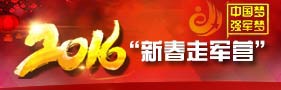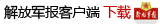军事改革是世界军事发展史上的经常性现象。世界军事大国根据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调整,围绕建立决策更科学、管理更高效、指挥更便捷的军事组织体系这一主线,不断推进改革。军事改革同时又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它是国家和军队领导层针对军事组织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主动进行的较大幅度、较为深刻的调整,是对军事组织的重大而有序的改造。军事改革既有规律可循,同时又是一个需要创新设计与强力推进的过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总结世界主要国家军事改革经验,对我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具有重要借鉴参考意义。
坚持以联合为导向,把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作为改革的主轴
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制胜的基本规律,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军队组织体系化、作战力量多元化、军事行动全域化的内在要求。美俄等大国军队瞄准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了艰难而又曲折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间,美军基于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在“统一军队领导指挥权”的大联合方向上不懈努力,经过三轮大改和无数小改,终于建起了目前的“国家指挥当局(总统和国防部长)——联合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职能司令部)——任务部队”的三级指挥链。第一轮改革是1947年到1949年,主要是创立以国防部为主体的领导指挥体制,设立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在战略层级上解决了作战指挥权不统一的问题,形成了现代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雏形。这一时期,军种仍主导参联会。第二轮改革是1953年到1958年,建立总统和国防部长对作战司令部的直接指挥关系,明确战区联合司令部在军事上的联合指挥权,把军种排除在作战指挥链之外。但军种对作战指挥的干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各军种利用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在作战指挥上继续操控作战司令部下属的军种组成部队,在决策流程上干预联合参谋部的工作。直到第三轮改革出台具有标志意义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从法律上明确了作战司令部司令拥有指挥全权后,军种才完全退出了作战指挥链条,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才真正得以建立。此后若干次小改,也都围绕如何提高联合作战指挥效率,对作战司令部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冷战后美军取得的几场局部战争胜利,同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密不可分。
俄军从冷战后爆发的几场局部战争中认识到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汲取叶利钦时期改革教训的基础上,俄军从调整总参谋部职能入手,以改造军区为重点,几经曲折,最终形成了“总统和国防部长——总参谋长——联合战略司令部/职能司令部——军兵种部队”的四级指挥链。第一步,俄军先对总参谋部进行改造。适度下放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权,取消其直接指挥战略方向作战的权力,同时保留对战略核力量、空天防御兵、空降兵和军事运输航空兵等职能领域力量的指挥权。这一举措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第二步,通过重组和改造军区,赋予军区领率机关联合战略司令部职能。此举意义在于,军区成为战略方向上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战略方向军种部队与军区司令员建立直接隶属关系。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取消军种作战指挥权。2012年,俄军解除了空军和海军总司令部的作战指挥职能,并将海军、空军和空天防御兵中央指挥所并入总参武装力量中央指挥所。近期俄军在收复克里米亚行动和叙利亚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表明了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成功。
美俄两国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由于国情军情不同,战略任务有异,最终所实现的联合程度与重心也不同。美国联合程度最高,军种彻底交出作战指挥权,退出指挥链;俄罗斯基本实施联合,军种交出绝大部分作战指挥权,只在维和、反海盗等领域保留部分指挥权。美国把联合指挥的重心放在联合作战司令部;俄罗斯把战略方向联合作战的指挥重心放在联合战略司令部,把职能领域的指挥重心放在总参谋部。但从发展趋势看,联合范围都正在由跨军种向跨领域拓展,联合层级也由战略战役级向战术级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