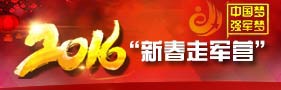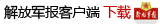坚持双重分工原则,把建设管理权与作战指挥权适度分离作为改革重点
现代管理和作战指挥是具有各自对象领域和规律要求的科学与艺术。二者内在机理不同,要求确立双重分工原则,从体制上科学区分建设管理与作战指挥两大职能,确保按各自规律组织实施;二者又密切关联,要求从机制上确保有机统一,确保“建”“用”结合、“建”以致“用”。
美俄等国均把划分建设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作为军事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58年美军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阶段性突破,正是因为初步划分了建设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从法律上建立了军政军令相对分离的领导指挥体制。经过随后20多年的实践和辩论,1986年的改革继续坚持这一方向,进一步明确了国防部、参联会、联合司令部、军种部的各自职能,真正实现了建设管理权和作战指挥权的相对分开。
俄军上世纪末军事改革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理顺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没能在国防部层面实现建设管理权与作战指挥权的分离。正如俄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尼古拉耶夫指出的,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能,“是控制整个军事改革进程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一步做不到,军事改革就无法推进”。2004年俄军剥离了总参谋部的大部分行政职能,实现了国防部内部军政军令的适度分离,此后改革才走上了快车道。
美俄等国从自身国情军情出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军政军令分离模式。美军在战区和军种部层面均实现了两大职能的相对分离。在作战指挥上,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主席直接指挥联合司令部;在军队建设上,总统通过国防部长和军种部对军队实施管理。在战役层面,联合司令部只对下属军种部队行使作战指挥权,建设管理则由各军种部负责,不需要通过联合司令部。俄军1998年曾提出区分两大职能的基本原则,即“在战略级指挥机关尽量分,在战役战略级适度合,在战役、战役战术和战术级则完全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军在战略级把作战指挥权尽可能地向总参谋部集中,把行政管理职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各军种总司令部和国防部其他机关。但在战役级,俄军原本想学美军,由军区(联合战略司令部)专司作战指挥,后在实践中发现,把军区完全排除在行政管理链之外,无法保证军种向其提供合格的作战部队,遂赋予军区较大的行政管理权力,规定军区必须执行“军种总司令在其职权范围内颁布的训令和指示”。
美俄等国还通过建立一定的制度机制,确保国家军政军令系统协调运行。比如,美国建立了参联会有效介入项目、预算和采办等资源分配领域的机制,确保作战需求对军队建设的牵引;联合司令部司令有免除部属职务、鉴定任职表现、召集军事法庭制裁等人事权,以及项目需求建议权。俄军在国防部建有实施顶层协调的部务会议,由国防部长、副部长,军种总司令等集体审议国防部最重要的问题,确保各部门活动的协调统一。部务会议通常由国防部长主持,根据议题,也可由总参谋长、主管战斗训练的副部长、主管后装保障的副部长等国防部副职主持,协调本领域的重大事务。俄军还赋予作战部门相关权力,确保军队建设符合作战需求。比如,俄军总参谋部享有组织制定国防计划、战场建设计划、战争动员计划等规划计划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