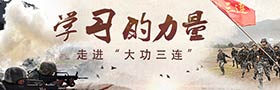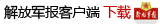(三)三种关于特朗普重返孤立主义的争论
特朗普是否会使美国回归或重返孤立主义,已成为持续争论的焦点。从当前的各种议论看,有这样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就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他的政策必然会使美国重新回到孤立主义的道路上。吉迪恩·拉赫曼指出:“孤立主义是特朗普思维中固有的倾向”;怀特指出:“特朗普拥有一套连贯一致的世界观”、“如果‘孤立主义者’这个单词有意义的话,他就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弗朗西斯·福山指出:“虽然特朗普本质上是一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内心深处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特朗普就是要改变美国罗斯福以来的政策和战略,将在“美国国内优先”(America First)的旗帜下减少美国的国际参与,从而对国际和平和稳定造成冲击。
另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即便有孤立主义倾向,但美国绝对不会重返孤立主义。“现实国际主义”的代表人物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国不可能有‘新孤立主义’的选项。这只不过是在不了解外交政策的人之间流传的一种幻想。”;佐利克指出:“特朗普这个习惯逐笔处理交易的谈判家,可能倾向于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外交政策”、“正如所有总统一样。他们对危机的应对必须体现出美国利益和领导力的战略框架”。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不论特朗普本人倾向如何,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和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在确定“美国道路”问题上会倾向于传统的战略轨道。重返孤立主义,既不是特朗普的固有思想,更不是当今美国的理想选择。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朗普既非“完全的孤立主义者”,也非“完全的国际主义者”。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也有人认为他是重商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等等,不一而足。持这种观点人认为“特朗普对外交政策的态度更像是混乱的即兴发挥,而不像是战略思维。关于其策略的最大问题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关乎过程,而非政策。”因此,正如基辛格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并没有提出世界观”。曾成功预测小布什政策的美国心理分析师麦克亚当斯(DanP.McAdams)指出:“特朗普表现出一种人们预计美国总统绝对不会存在的性格轮廓”他“决策风格会像20世纪70年代早期尼克松和他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国际事务中所展现出的精明现实政治风格,模拟尼克松政府丝毫不留情面的国内政策”,不过他“似乎具有类似的强硬与战略实用主义立场但冷静与理智看来永远也不适合他”,更“可能会为获得丰厚回报而孤注一掷,而回报就是竞选口号说的那样,让美国重新伟大”。
从上述争论来看,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而他的政策也成为争议的核心;特朗普具有争议的政策倾向,又决定了他必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总统。在“特朗普与谁最像”的议论中,他的名字被与那些“消除了人们对于‘可接受政治’限定”的人物,如休伊·朗(HueyLong)、罗斯·佩罗(RossPerot)、珀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等人联系在一起;也被与美国历史上的那些倡导有争议政策的人物,如20世纪30年代的考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50年代的乔·麦卡锡(Joe Mc Carthy)、60年代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等人相提并论;更与被称为“民粹主义者”的现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等人相类比。这样的议论,总体上反映出对特朗普孤立主义政策倾向深层次的担忧和对美国战略方向转变的极大忧虑。这种忧虑的潜台词就是:“害怕的不是敌人的战略 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四)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与现实孤立主义
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政策,它“既可追溯到这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位置——这个国家因两个大洋而一直与其他列强基本隔离 也可追溯到它的建国之父们的愿望那里——即美国的政治实践不应该因参与欧洲权力政治平衡而被腐蚀”;作为一种战略,它“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执行时间最长的大战略。除了几次短暂的例外,孤立主义战略从1789年到1947年一直垄断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历史上,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这样的模式:“在不加选择地远离权力政治观与同样不加区分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两端之间钟摆似地摇摆”。这种两极摇摆的“精神分裂症式”方法,体现出美国战略“避实就虚”(Strength-through-Weakness)的实用原则,但“这两个极端有共同的意图,即避免受来自国外麻烦的威胁”。
美国传统孤立主义有四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外交和军事“不结盟”原则。这一原则的初衷是为阻止美国卷入欧洲的冲突,避免参与联盟带来的危险,而不是要求美国不参与国际事务;第二条是外交全力维护美国国家主权的独立地位和政治文化发展不受外来影响的环境。第三条是强调美国单方面行动的自主权。第四条是坚持美国不得参与国外的战争。这些原则,又建立在这样的几种信念基础上:一是相信美国以外发生的事情对美国不构成军事威胁;二是相信美国军事力量若不发动战争的话不可能影响国际环境;三是相信不值得为达到塑造国际环境的目的冒发动战争的代价和风险。这些原则和信念,成为孤立主义的基本信条。二战后,尽管新孤立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孤立主义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思想,但不论是保守派新孤立主义还是自由派新孤立主义,都将“相信美国具有战略免疫力(strategic immunity)、相信经济发达不需要投放军事力量,以及认为美国海外军事冒险会耗尽自身能量”等作为共同的理论基础。不同之处仅体现在:保守派新孤立主义认为应将军事力量作为其实现外交目标的必要的基础和后盾;自由派新孤立主义则强调应遵循“外交政策从国内政策开始”的信条,有选择地规范和评估必要军事力量的限度。
尽管孤立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但在文化和商业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孤立主义不是“闭关锁国”式的与世隔绝,也不是“自给自足”式的自我满足;孤立主义不等同于不使用武力,而是避免无节制、无原则的军事介入;孤立主义不是限制美国的行为、束缚美国的影响,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最大限度地维持美国道义至高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孤立主义战略是一种“单边主义”战略,是一种“袖手旁观”战略;作为战略的一种延伸,它与“有选择的干预”战略和“离岸平衡”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战后新孤立主义的消长与美国霸权地位的消长是紧密相连的。作为世界的霸权国,“美国不只是一个仗势欺人的强大国家——尽管它确实如此。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还体现在语言、观念以及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s)上。广泛的制度联系使美国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密切联系,并提供了一种原始的治理体系(aprimitive governance system)”。美国依靠这种“制度霸权”维持着美国的优势地位收到了与战前孤立主义战略同样的效果。但是,战后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霸主地位遭遇到目标与手段、义务与资源间紧张关系的挑战。从而使美国大战略争论一直聚焦在是确保霸权地位的绝对性还是相对性、是美国支配还是美国领导、是以维护国际霸权秩序为重心还是以美国国内需求为重心的问题上。在不同时期,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评估、对美国利益的界定以及对美国威胁来源认识的变化,都使美国不断地在新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立场间摸索和调适可行的战略。
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战略的收缩、9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优先的选择等来看,现今特朗普的崛起以及孤立主义的倾向并非“史无前例”。之所以特朗普广受非议,原因在于他可能会挑战并瓦解自罗斯福时代美国创建的国际秩序、要改造共和党的政治信条,并可能要重塑美国霸权的逻辑。这直接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要不要继续维护美国霸权。因此,不论孤立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都对他的政策予以批评。怀特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和平和稳定的冲击将会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罗伯特·卡根称“他的目标是以美国为先,这意味着长达70年的美国世界秩序更加接近终结”;福山则更进一步认为“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标志着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也是如此。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时代”。西方这些权威学者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霸权终结”的断言,充分地表明他们对“霸权缺失”的忧虑与恐惧,以至于无法摆脱依赖霸权的情结。从整个世界秩序的转变看,特朗普现象并非是美国“独特”的现象,英国脱欧、欧洲民粹民族主义的泛滥等都在悄然改变着对秩序的定义。特朗普现阶段的政策主张也并不意味着完完全全地“回归”传统的美国孤立主义,或许如卡根所言的那样:他可能“重返国家唯我主义——以狭隘得多的方式定义美国利益 不愿参与世界事务。换句话来说,美国或许会再次开始像一个‘正常国家’那样行事”。但是。即便是这个“正常国家”,也对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霸权惯性思维”构成了挑战。从这一点上说,特朗普的冲击还仅仅是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