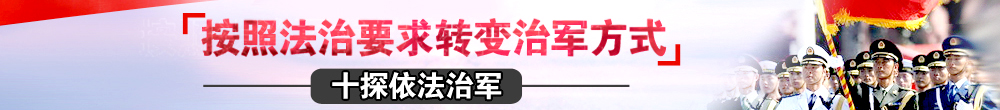2、文学是携带、传播英雄文化的主要工具,同时又是催生英雄文化的使者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中国人的童年大都伴随着英雄的故事和英雄的梦想成长,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那样战天斗地的神话英雄,到各个时期的战斗英雄……更多的时候,英雄不再是存放在凌烟阁上的牌位和封神榜上的名册,而是行走在原野和河流山川之间的风,而是传送在书斋和村头集市的雨,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携带传播,以潜移和默化的形式生根开花,成为中国性格的重要特征。
文学是携带、传播英雄文化的主要工具,同时又是催生英雄文化的使者。每当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渴望英雄出现——通常,是以文学的方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敦促实现“国运强盛”,一批“呼唤英雄”和幻想“坚船利炮”的小说应运而生,比较典型的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陆士谔的《新中国》《新野叟曝言》和吴沃尧的《电术奇谈》等等。在这些作品里,古代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智勇双全的战争将领重新回到了当代,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官兵又奔突在杀敌驱倭的战场上。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已经突破了农耕文化背景下的英雄模式,有应对未来战争的远见卓识,有向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行动,有指挥科技战争的能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带有科幻性质的关于武器装备的预测,很多都是建立在科学常识的基础上,在今天不仅得到了实现,而且更多都已经得到了超越。用当代眼光来看,这些作品是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内,文学对英雄、文化对国家命运的一次直接关注,一次文学和文化正能量的集中爆发。可惜的是,在那个蒙昧的时代,被摇摇欲坠的朝廷视为“奇技淫巧”,斥为“荒诞不经”,因而受到冷落,这不仅是文学的遗憾,也是英雄的遗憾,终归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晚清社会,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国力衰弱到一触即溃,民心涣散成一盘散沙。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梁启超,几近绝望。何以救国?呼唤英雄!英雄何来?梁启超把目光投向文学,“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过文学改变中国人,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八亿神州尽舜尧”的境界。
与梁启超观点接近的还有鲁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也认为“文艺”——其实更多的是指文学——可以提供思想基础,可以改良民族精神,这就是他弃医从文的原因。
梁启超和鲁迅文学救国的梦想在他们的时代未能实现,不是梁启超和鲁迅的观点出了问题,也不是文学出了问题,而是文学生成的土壤出了问题。在清末民初那个病入膏肓的躯体上,文学不可能妙手回春。
但这并不等于文学没有力量,文学的力量无所不在,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地久天长。文学和文学教育,其独特的审美功能、慰藉功能和激励功能,以其思想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艺术感染力,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直至这个苦难的民族于病痛中苏醒,重新找回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