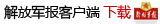三姨如母
(散文)
乔林生
三姨是我母亲的小妹。
外婆家穷。大概八九岁,三姨便从无定河边的一个山村来到我们家生活。那时,母亲已经生下我的两个哥哥,三姨一边上学一边帮着母亲料理些家务。父亲经常出差在外,母亲有这么个跑前跑后的小妹妹,真是顶用。可一旦父亲回家,家里住的地方紧张了,三姨就得到关系比较好的左邻右舍借宿。有一次,父亲半夜三更才到,不知为什么事发了很大的火,三姨吓坏了,哭着爬起来穿衣服往外走。母亲给我讲这事的时候,红着眼圈。不过,母亲又说:“别看你爸狗食脾气,可对你三姨,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是的,一直是父亲供三姨上学和吃穿用度,并资助外公家度过食不果腹的饥荒岁月。
三姨个性倔强。小时和外公吵架,性情粗暴的外公打了她,她一气之下从悬崖上跳下,差点丢了性命。三姨对我们兄妹却是很温和很温和的,从来不使性子耍脾气。我出生后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没奶水,上街买奶粉奶粉断,买炼乳炼乳断,三姨帮着母亲捣碎小米,熬成糊糊喂我。由于缺乏营养,我两岁还不会走路。母亲又生下妹妹,我是在三姨的背上长大的。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三姨用她节省下来的几毛钱,带我看戏看电影的情景。
那年,三姨十八岁,看上了邻居家的一个男孩。父亲对那种长相漂亮腹内空空的公子哥儿很反感,劝三姨不要找这种人。可三姨执迷不悟,态度非常坚决地跟那个人结了婚。
我那时也就是六七岁吧,每回去城南,总要去三姨的丈夫家看三姨。见我们来了,三姨开始生火做饭,她婆婆看见便不高兴,她也不管,总要让我们吃了饭再走。后来,母亲坚决地不让我们到三姨家去了。
不出父亲所料,三姨嫁的那个男孩果然靠不住,没有多久就把地方剧团一个戏子的肚子搞大了。三姨岂能容忍这等肮脏事发生,为此和丈夫吵嘴打架,吵来打去最后离了婚。三姨又回到了我们家。全家人十分高兴和庆幸,三姨总算逃出了虎口。
后来,三姨做了几年乡村教师。每到假期,她就回城。到了晚上,等我们几个孩子钻进被窝,三姨便和母亲坐在灯底下,一边做着做不完的针线活,一边说着家长里短的话儿。总是三姨的话头特别长,讲农村发生的事,讲教师们中间的事,讲学生们有趣的事,讲男婚女嫁、生儿育女的事,讲着讲着,我们安静地睡着了。
三姨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重要成员。有一年,母亲得了重病,需要输血。那时县医院没有血库,父亲的血型不符,是三姨挺身而出,用自己的400CC鲜血救了母亲一命。从此,三姨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红润和美丽。尽管这样,小巧玲珑的三姨还是很引人注目。母亲往院期间,医院的一个美男子向她求婚,母亲都觉得高攀了人家,三姨也愿意。不料,外婆突然杀到,一听那个美男子是外地人,坚决不答应,连人带礼物扫地出门。那个美男子受此冷遇,不想再谈了,气得三姨伤心落泪。
于是,三姨想离开当地,到远一点的地方工作。不久,一家大油矿来我们县城招收工人,三姨兴冲冲报了名。那时能到油矿当个工人,是天大的喜事,竞争相当激烈。不知什么人在招工的头头那里使了坏,三姨莫名其妙被取消了资格。
回家后,三姨愤愤不平。父亲听完缘由也急了,去招工地点找人评理。到现场一看,父亲乐了,招工的负责人原来是父亲在省党校学习时的同学。最后三姨不仅去了这家油矿,还分配在相对轻松的化验室工作。
那时我已上了中学。每到暑假,我便乘车到三姨那里住些日子。油矿食堂的饭菜比家里好,但也有粗粮、杂粮。三姨总是省下细粮票给我,总是给我买肉菜。闲暇时,三姨的男同事便带着我去澡堂洗澡,带着我满世界瞎逛,那真是少年时值得回味的一段幸福时光。
当时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代名词,很牛,用深蓝棉布做的茄克式的工作服也十分时尚流行。三姨矿上每人只发一件,样式好,质量也好。我当时不好意思开口,后来就写信问她要。过了一段时间,三姨果然给我寄来了。那件茄克工作服我穿上十分合适,父亲又花十四元钱给我买了一双白底蓝帮的回力鞋,这一身打扮在我们中学引起不小的轰动,有个女同学还为此多次暧昧地向我传递纸条呢!至今一直喜欢穿茄克衫,是不是就是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种下的癖好?
三姨又结了一次婚。有一天,我放学后正在路边走着,一个高高大大推着自行车的人问路:小同学,某某某家住哪里?一听是我爸的名字,我急忙跑回家向母亲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后来母亲告诉我,来客曾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名骑兵,刚刚复员回来,分配在邻县法院工作,正在和三姨谈恋爱。这人长的浓眉大眼,性格憨厚老实,母亲说使得。
三姨结婚时,我和二哥去男方家参加婚礼。也就是两家的亲戚凑在一起吃顿饭罢了。
下午,蓝天丽日,水清草绿,三姨和三姨夫领着我们在河边游玩。我们在前面跑,他俩一高一低慢慢在后面跟着,说着别人听不清的悄悄话。偶而,能听见三姨悠扬、动听的歌声传来。
以我的眼光看,三姨干净利落,知书达理,是个完美无缺的人,应该找一个更好更有本事的男人。可母亲说,你三姨是二婚,只要人家不嫌弃,能和她好好过日子,我们也应该知足了。
婚后,三姨生了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她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可对我们兄妹,仍然和从前一样。
我十七岁参军上了青藏高原,三姨特别担心,总是来信千叮咛万嘱咐,生怕我有什么事处理不好,或者有个什么闪失。我说我已经长大成人,用不着三姨操心了,可三姨依旧是三姨,我吃啥喝啥穿啥戴啥,都和她息息相关,都让她牵肠挂肚。
父亲去世后,母亲发病,导致半身不遂。我在外地,弟妹们各有各的困难,三姨便替我们承担起照料母亲的责任。有时,母亲在她家一住就是半年,我心里过意不去,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后来,我几次把母亲接到北京生活,我住六楼,没有电梯,母亲下楼上不去,上楼下不来。我们上班后,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就像关了禁闭,整天唉声叹气,烦躁不安,我只好一次次把母亲送回家乡。可没过几天,妹妹会来电话说,三姨又把母亲接到她那里住去了。三姨也是大儿大女一大家子人,住房紧张,长期拖着母亲这个包袱,三姨夫会怎么想,亲戚路人会怎么想。给他们家增加麻烦、增添矛盾是明摆着的事嘛!
重病在身的母亲脾气越来越怪,尽管三姨尽心尽力照顾,可她有时还不领情。油矿上的邻居见了母亲问:“你妹妹对你怎么样?”母亲不耐烦地挥挥手:“别说了,别说了。”那意思不言自明。我们要给三姨些生活费,母亲也不让,说:“她那么小到我身边,我把她养大,也没见她给过我什么钱。”三姨知道了这些事,心里挺不好受,觉得挺委屈,可说归说,恼归恼,对母亲知冷知热的人最后指定还就是她。
2002年母亲节那一天,患病十四年的母亲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我年年回老家看母亲变成了年年回老家看三姨,三姨如母啊!
病灾还是瞅你最亲的人下手。没过两年,三姨也突患脑血栓。经过一段时间治疗,饮食起居、日常生活没受大的影响,恢复得比母亲要好很多。这期间,她也来北京看过病,我带她和三姨夫把能看的名胜古迹都看了一遍。
真应了那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三姨和母亲一样,都是在虚岁七十三岁那年去世的。三姨心梗,延安市医院的庸医却当成胃痛治,硬是把人给耽误了。在无尽悔恨中,在瓢泼大雨里,我们哭嚎着把三姨抬到山上,埋了。
整整五年过去了,对三姨的思念如同对母亲的思念,从来没有减少一分。特别怕过母亲节,怕勾起对亲人痛彻心扉的思念之情。
走不出的悲伤千万里,留不住的母爱千万缕。又到母亲节了,三姨,您在那边还好吗?您见到您的姐姐——我的母亲了吗?她过得还好吗?她还老是唉声叹气吗?你们姐俩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围坐在灯底下,一边做着细细的针线活,一边拉着绵绵的体己话?还有父亲,他在那边还好吗?还整天下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顾不上回家吗?
三姨,昨晚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神情自若站在无定河边唱那首你在世时经常唱的歌:“一把拉住亲人的手,亲人的手,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2016年4月25日改定)
作者:解放军报社文化部原主任 乔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