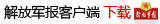南侨机工驾驶大货车行驶在滇缅公路上。
“华侨统统有”
1939年2月,南洋各大报纸刊登了南侨总会招募华侨机工的《通告》。从《通告》内容看,招募条件还是很严格的。首先,要求机工熟悉驾驶技术,并持有当地政府发的驾驶执照。第二,招募机工要求是20至40岁之间的年轻人,并要通晓中国语言文字,无不良嗜好。第三,凡应征者,必须有当地人或者商店介绍,“知其确有爱国志愿方可”。
夏玉清告诉记者,当时南洋情况非常复杂,日本人和汪精卫的人都在拉拢华侨,因此政治上可靠非常重要。
《通告》发出后在南洋华侨中掀起了一股回国抗日、报效祖国的热潮。
上世纪80年代,南侨机工蔡汉良经人介绍找到在华侨大学教书的林少川。当蔡汉良表示自己是应陈嘉庚号召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中的一员时,林少川有些吃惊。林少川告诉记者,他虽然教的是“华侨史”课,但是从未接触过南侨机工,对这段历史也所知甚少。
蔡汉良成为林少川接触的第一名南侨机工。后来,在陈嘉庚侄子陈共存先生的支持下,林少川跑遍了西南几省,访问了许多南侨机工,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
1939年8月,泰国华侨蔡汉良看到招募机工的《通告》,觉得自己既会驾驶,又会修车,而且内心充满了报国热情,符合《通告》中的一切条件。为了怕家人反对,蔡汉良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报名。没想到,他中途撞见叔父的好朋友王联辉。为了挽留蔡汉良,王联辉甚至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并要将自己名下的16辆车送给蔡汉良,让他开一间客运公司,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蔡汉良报名回国的决心。他谢绝了王联辉的好意,毅然踏上回国之路。
刚刚结婚不久的刘瑞齐报名后,与同伴们一起剃了个光头。当妻子看到他的大光头时敏感地问:“莫非你也想回国?”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启程,刘瑞齐向妻子撒了谎,说剃光头只是为了方便敷药。当天夜里,刘瑞齐给妻子留下一封书信,悄悄上路。谁知道,这一别竟成永诀,他离开不久,妻子便忧郁成疾,撒手人寰了。
林少川说,在南侨机工群体中,像蔡汉良、刘瑞齐这样,瞒着家人不辞而别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四名女性女扮男装参加到南侨机工的队伍中。其中一名叫白雪娇的女教师,在辞别父母的信中写道: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里起着数次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豫、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后来,这封家书被刊登在马来亚《光华日报》上,鼓舞了许多爱国华侨。
1939年2月18日下午3点,第一批南侨机工服务团80人从新加坡乘船出发,返回祖国。临行那天,新加坡码头上人山人海,街道上横幅招展。送行的人们将帽子掷向空中,场面热闹非凡。由于送行的人太多,码头上的木桥都被挤塌了。
据统计,1939年2月至10月间,共有3192名南侨机工分9批回到祖国,奔赴抗战前线。
当时,在南侨机工中流行着一句口号“华侨统统有”,意思是为了抵御日寇侵略,华侨都走到一起来。后来,只要一说起这句口号,他们就知道彼此是南侨机工。
不愉快的初遇
满怀报国热情的南侨机工回到祖国后,并没有立即投入到军事运输的工作中,而是被送入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受训。
训练所设在昆华师范学校内,场地狭窄,条件简陋,没有专门的食堂,也没有专门的教室。几千名机工挤在一处,不得不自办伙食。机工们脱去西服,换上军装;剪掉油光可鉴的分头,每人剃了一个大光头,与刚抵达昆明时判若两人。
训练所教育长张炎元这样描述机工们的生活:“早粥时间,没有旁的菜,只有腌菜,白萝卜之类,大家胃口都不坏,起码三大碗稀饭到肚。吃快些的,有吃上五六碗的,菜吃完了,只好啜白粥。”
训练科目分军事、政治和技术。南侨机工虽然都是驾驶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士,但是云南多为山地,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路况奇差,与南洋的环境天差地别,进行一些山地行车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对于军事训练南侨机工们就不那么认同了。到了训练所后,机工们穿上统一的军装,吃饭时一声哨响就得举筷猛吃,几分钟后哨子再次响起,没吃完的也得把筷子放下。见到长官要让道、立正、举手、注目、礼毕。每天早上出操一个小时,立正、稍息、跑步、敬礼、卧倒……完全像训练新兵一样。
许多南侨机工自幼生长在南洋,不少人家境优渥,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甫一进入训练所,这种军事化管理的模式让他们很难适应。
其实不只是机工们不太理解,就连陈嘉庚本人也对这套军事化管理颇有微词。1940年秋,他回国考察期间,一次,一位曾在新加坡做医生的机工见到陈嘉庚等人立刻举手立正行礼。过了一会儿,见到别人到来,他又郑重其事地举手立正行礼。
当时,陈嘉庚便感到十分不自在:“此种繁文缛节,为在洋及回国后未曾见。延安无阶级固勿论,便是重庆及各省县亦未见过。岂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所特有者乎?”
在西南运输处筹建训练所之初,对于要不要搞军训也有过争论。西南运输处秘书冯君锐认为,司机不是兵,培训应该主要集中在山地开车方面,没必要搞列队、集合、行进之类的军事训练。冯君锐回忆,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同意,但是事后副总队长薛文蔚还是像训练新兵一样训练机工们。
这样一来,初来乍到的机工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一方面不适应训练所的训练模式,另一方面与昆明当地军民也多有摩擦。
闹得最凶的一次是1939年四五月份,由于语言不通和买卖纠纷,机工们在云南有名的云津市场跟商贩和军警大打出手,机工们甚至抢了军警的枪械。训练所对此非常头疼,于是决定让机工们改为每周一放假,减少市面拥挤,避免纠纷。

马来西亚最后一位南侨机工李亚留刚刚去世。
滇缅路
经过两个月不太和谐的训练,南侨机工终于要上路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经畹町,直通缅甸境内的腊戌公路线,全长1146公里。
七七事变之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就曾预言,一旦中日之战全面爆发,日军必然会断绝我国东南港口。那时候联通外部、输送物资的唯一出口只有滇缅一线,因此应该赶紧着手修建滇缅公路。
1937年11月,战火已烧到华东,国民政府连忙委托云南省政府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穿越横断山脉、怒山、高黎贡山三座大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三条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弯,修建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80年前,云南彝、白、傣、苗、汉等十个民族的15万民工,愣是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短短8个月时间,将滇缅公路修建完成。当年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报道了滇缅公路修通的情况,并称:“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
滇缅公路虽然通车了,但非常简陋,路面基本上是用碎石铺就,经常塌方。
后来,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在《血路》一书中写道:
惠通桥两岸崇山峻岭,盘旋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狭窄难行,道路弯多陡峭,雨季时路滑难行,随时有翻车的危险。路基松软,有些路段狭窄,特别是雨季道路难行,“一雨便成冬”。滇缅路频繁塌方,给汽车行驶运输带来巨大的困难。
谭伯英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滇缅公路根本算不上是一条公路,充其量只能算马路,而事实上连骡马也不愿意走。
南侨机工被分为17个大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日夜兼程地行驶在这条连骡马也不愿意走的路上。车队装上货物从缅甸腊戍出发,开往终点云南昆明,全程一般要走6天以上。司机们白天开车,晚上在驾驶室里睡觉。由于他们大多开的是道奇汽车,所以许多机工幽默地称之为“道奇旅馆”。
在滇缅公路上行驶困难重重。
上世纪80年代,南侨机工李荣竹向林少川回忆,滇缅公路上崇山峻岭,迂回重叠。车队盘旋上山,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谷大川。沿途坡陡弯急,惊心动魄,车毁人亡的惨剧随时都会发生。为了避免翻车,机工们想了许多办法。如果上下陡坡又遇到急转弯的窄路,他们就在急转弯的地方铺一块木板,前轮开过之后,后面靠外的轮子正好可以从木板上轧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后轮悬空而翻入山谷了。
即便想尽办法,滇缅公路上的翻车事故还是层出不穷。据夏玉清统计,仅1939年4月至11月间,因车辆故障、山路崎岖、雨天路滑发生的翻车事故就达24起。华侨机工殉职情况表上,事故原因一栏经常会出现“覆车”两字。
1940年夏,南侨机工林树容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将一位牺牲机工的遗体运回队部,此人正是与林树容同一批回国服务的新加坡机工吴世光。
傍晚时分,他来到吴世光翻车的事故现场。吴世光的遗体已经被人从山谷中吊上来停在路旁。只有21岁的林树容,在南洋从没接触过死人,现在让他独自一个人去运尸体,他心里未免有点胆怯。可是,当他看到吴世光的遗体,想起平时的情谊,一下子忘记了害怕。他用毛毯把吴世光的遗体包裹好,抬上卡车。偏巧路上车子又抛锚了。三更半夜,林树容一个人被困在车中,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他害怕极了。他暗自祷告战友的英灵为自己壮胆。
上世纪80年代,独自寻访健在南侨机工的林少川,经常要一个人穿梭于西南边陲小城。每当他害怕时,他都会想到林树容一个人向战友英灵祷告的场景。他对记者说:“这样一想真的可以壮胆哦。”
在滇缅路上,南侨机工不仅要面对车祸的危险,还要面对另一个无形杀手——疟疾。云南山区自古就流行着一句俗语:“要过瘴疟坝,先把老婆嫁”。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如果得了疟疾几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机工许志光曾这样回忆,他被“疟疾蚊”咬叮患上“打摆子”,发冷时即便盖上重被、裹着毛毯也无济于事。幸亏机工战友献出印尼筹赈会送来的“金鸡纳霜”,才转危为安。
据统计,仅1940年在腊戍医院就医的南侨机工就达百人以上。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在报告中写道:“机工、司机,患恶性疟疾者比比皆是,在是处服务之华侨机工皆现面色清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
有人说,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工共抢运了50万吨军需物资。研究过相关档案的夏玉清告诉记者,档案中并没有确切记录过南侨机工抢运物资的数量,也许比这个数字还要大。
1940年,日本在研究中国军力变化的数据后发现,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军力反而比1938年增强了,其中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其他火炮2650门。这显然与滇缅路上日夜奔驰的南侨机工密不可分。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成立了“滇缅公路切断委员会”。从1940年10月起,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对滇缅公路狂轰滥炸。南侨机工们处在了战火的最前沿。
白天遇到敌机轰炸,机工们利用地形将货车隐藏起来,夜里再关着灯摸黑行驶。
1941年1月,日军轰炸机炸断了滇缅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冲——功果桥。为此,东京电台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
当时,运载物资从保山返回下关的王亚六刚好目睹了。功果桥的铁索桥和吊板被炸成两截,桥两边好几百辆车子无法通行,堵得水泄不通。为了尽快抢通功果桥,机工们纷纷出谋划策。他们根据浮力原理,将几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连起来,然后铺上木板。经过10个小时的奋战,一座长达300米的临时浮桥做成。功果桥被炸断10个小时后,堵在桥两岸的大货车通过浮桥安然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