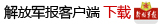模式探索
丁刚:西方思想界目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治理模式的讨论,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都是战后从未有过的。有专家称此为“人类对自身文明发展认识的一个拐点”。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中国元素”开始进入类似研究的参照系。比如,美国学者福山提出的维系现代政治秩序的三元素:强大有效的国家(中央权力)、法治以及回应民众要求的可问责民主,就总结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国家治理能力,也就是领导力,可以说这是一个“呼唤领导力之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新年专刊首篇文章提出,西方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领导力下滑。2014年西方学者对未来全球治理前景的忧虑,以及对世界秩序可能陷入混乱的担心,其实都与西方国家领导力下降相关。中国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显示出了生命力和影响力。
温宪:今年美国两党政治僵局持续,对美式民主制度的反思也成为显学。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司法和立法部门对政府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美国人一贯信不过政府,由此就催生了立法部门解决行政问题的局面,导致成本升高、效率低下。美国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
胡里奥·里奥斯:欧洲当前面临的危机不仅仅限于金融或经济危机,而是体制危机。现存体制漏洞已经危及了民主的本质,民主从民众利益的代表和象征转变为维护大财团利益的政治借口,忽视了社会凝聚力和公平正义。民主成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大型公司的工具。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财团控制了权力,权力不再属于人民,民主赤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严重。这需要我们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贝尔特朗·巴迪:体制危机逐渐成为世界多国的“共同分母”,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巴西、印度、南非目前都面临强大的政治体制抗议。我认为,这场政治体制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经济危机的解决,也要通过对政治结构必不可少的改革。
托马斯·皮凯蒂:经济开放、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如中国的发展。但同时应保障社会各阶层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经济增长不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
民主形式不应只有一种模式。我不认为欧美的选举式民主政治是唯一可行的民主方式与组织方式。我对中国的整个成功发展故事很感兴趣。我不预言西方的民主方式能继续很好运转,因为有许多问题它解决不了。法国与欧洲可以从中国学习许多东西,中国也可以从欧洲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丁刚:拉美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新兴经济体广泛面临“脆弱中产”挑战,在外部经济动力减弱、内部经济转型困难的双重压力下,国家治理难度不断加大。目前全球有40%的人口处于“脆弱中产”之列。具体地说,发展中国家有近30亿人每天靠2到10美元生存。这部分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能否进一步改善,直接决定新兴经济体的命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步入了选举困境。这些国家的最大票仓是中下层,只有照顾到这部分人利益,才能得到更多选票。由于中下层与中上层的利益出现了矛盾,选举的结果往往是社会的撕裂,政府的决策力和执行力趋弱。
郑永年: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选择了西方模式,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新加坡选择的是自己的模式,也在不断平衡资本和社会的力量,国家主要通过将企业和政府投资的收入通过各种形式分配给百姓。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善,任何模式都要随着社会的改变不断发展。中国的模式有潜在的优势,有自己的发展逻辑,通过改革能够发挥出更多优势。
胡里奥·里奥斯:我十分认同新兴经济体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治理模式。中国通过坚持不懈的改革向世界展示了其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中国如今正在追求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经济增长以及公平正义,并极力将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全球发展趋势相结合,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