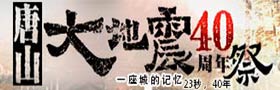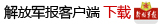政论人才何以成
——从刘新如政论文集《大道行思》说开去
■蔡惠福
刘新如是军队媒体新闻评论和理论宣传大家。近几年来,他因工作的需要,把重点放在了政治性评论文章——政论的写作上,紧随着强军建设的进程,撰写了不少产生广泛影响、得到普遍好评的政论佳作。其中有些一经发表,就如巨石投水,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最近,有幸读到了他的政论文集《大道行思》,受教之余,对军队媒体在新时期如何培养政论人才,促进政论的进一步繁荣产生了一些想法。
“雕龙”与“雕虫”并举
刘新如撰写的政论《“睡狮”的醒来——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与伟大民族觉醒》于2015年1月7日发表后,《解放军报》不久刊发了一则评报文章,称此文是“凿开历史冰河的‘利斧’”,具有“大视野”“大气魄”“大情怀”“大思路”等等。我们不必计较作者用了这么多的“大”字是否有些奢侈,但透过刘新如这篇政论,确实可以领略到他的高手风范。
政论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时评,也迥异于风片雨丝般的微型言论,更不会如梁启超所说,“将注意力放在‘邻猫产子’之类的琐屑事情上”。主题重大是它最大的特征,它总是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观点和认识,以启迪、引领社会的意见、思想和舆论。它的所议所论,常常关乎社会发展的走向;它的表达形式,不乏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它是评论中的宏大叙事,称其为“高大上”也无不可。这种新闻评论中的重磅作品,自然是非大手笔不能为,必须是深具才识、功力老到的大手笔才能驾驭统摄。古今能做政论文章者,大都是新闻评论中的高手大家。
古代对写文章做学问有“雕龙”和“雕虫”之说。所谓“雕龙”,就是做大事,创作大作品,做大文章;“雕虫”则是指做小文章,写小作品。我国著名古汉语专家王力先生曾将自己的书房名之为“龙虫并雕斋”,意思是说自己“雕龙”与“雕虫”两样都要干,必须两样都能干。王力先生确实是一位“龙虫并雕”的大家,他一生“雕龙”像“龙”,“雕虫”像“虫”,既写有《古代汉语》与《汉语诗律学》这样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又有《诗词格律十讲》之类的小册子,还有《西洋人的中国故事》与《夫妇之间》这种杂记小品。我们搞新闻评论的同志也许很难与王力先生相比,未必能做出他那样的事功。但他这种“龙虫并雕”的精神追求,则是我们所需要的。做新闻评论这一行,也需要有既能“雕龙”也能“雕虫”的本领。也就是说,既要能做好短小精干的时评短论,也要有撰写政论这种评论中重磅作品的本事;既要能写好“千字文”,也要能做好“万言书”。
我们丝毫也不应该轻视短论时评这些“千字文”的作用和地位,决不能将这些“雕虫之作”视为“壮夫不为”的“小技”。时评短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新闻舆论中的言论利器,而且许多千字短文其价值、其影响丝毫也不亚于那些鸿篇巨制,有谁能说鲁迅杂文的力量弱于他的小说呢?然而,当社会的发展、军队建设的需要以及媒体的变革,使政论成为新闻舆论阵地上一支不可或缺、甚至是其他文体难以替代的力量,其重要性不断地显现出来时,每一个从事评论工作以及有志于评论的同志,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回应这一新的需求和期许,苦练政论写作的本领,努力攀上政论这个“新闻的最高台阶”。
练就“上帝之眼”
所谓“上帝之眼”,是一颗被三角形及万丈光芒所环绕的眼睛的图像,这个图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常可见到。因为“上帝之眼”又称全视之眼和全知之眼,含有上帝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俯视、凝望、观察着地球上的一切的意思,所以,就有新闻传播研究者和从业者将其借来,喻指新闻工作者必须像具有一双全视、全知的“上帝之眼”那样,站得很高,视野宽阔,目光深远,能够把握全局、了解整体、认清大势,精准地洞察变化。撰写政论文章也需要练就这种站得高、看得远、目光准的“上帝之眼”——也许我们永远都难以真的拥有,但必须持之以恒,孜孜以求。
政论的性质功能决定了它必须主题重大重要,必须议大事、说大事,还要能见人之所未见、难见,发人之所未发、难发,把关乎社会发展走向中的大问题、矛盾关节点上的要害之处抓准、看透、论说清楚。因此,它要求作者必须比做一般的评论文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深、更准。也就是说,政论作者必须更有眼光、更有识见,有更强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眼光和识见,是政论作者素质能力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素质能力之“魂”。有些被称为“文胆”的顶级政论家,异乎常人的识见常常最为人称道。
透过刘新如的那些政论作品,可以看到他在努力地要求自己做一个优秀的社会生活的观察者、社会问题的发现者、社会现象的思考者。试想,如果没有对国家和军队改革建设进程的全面了解,没有对强国强军征程中困难问题的深刻洞察,没有对“正在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的深入分析,他能够写出《论信仰与作风》《中国梦也是强军梦》《甲午的殇思》及《历史的拷问》等拨动时代之弦、回应社会关切,引发人们在一片喧嚣之中沉静下来认真思考的力作吗?
一个政论者要练就“上帝之眼”,就要一刻不停、毫不懈怠地紧跟时代、关注现实。他还必须吃得了、受得住刻苦学习之苦、刻苦思考之苦、刻苦调研之苦。在艰苦的学习中培养理论家的学养,在艰苦的思考中锻造思想家的气质,在艰苦的调研中提升作为媒体人的政治敏感和务实精神。如此,才能心怀天下,俯瞰全局,以博大深透独到的眼光,从历史和现实的观照中,从中国和世界的比较中,从宏观和微观的转换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抓住最为关切的问题,写出胜人一等、黄钟大吕般的文章,成为真正的政论高手。
“论”不服人誓不休
所谓政论,重点在“论”,关键在“论”。政论的文本写作,是在“论”的过程中完成的,受众对政论的接受,实质上是对“论”之过程特别是对“论”之结论的接受。因而,“论”的能力也是政论作者的核心能力。而政论的“论”,更多的是论说道理,因此“论”的本事,其实也就是讲道理的本事。读刘新如的政论,也可以看到他在讲道理上表现出的功力。
天下所有属于“讲道理”一类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强烈的指向,就是要使所讲的道理让人信服。所有“讲道理”的文章的作者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沿着这个指向去实现这个目的的。只有受众认同了、接受了所阐述的观点,所叙说的道理,并将其内化于自己的认识思想之中,才能算是最终实现了政论文章的传播效果。政论文章无论块头多大,在媒体上位置多么突出,如果所讲的道理不能服人,没有被大家认可接受,那也是无效传播抑或低效传播。
所以,政论大家们都有一股“论”不服人誓不休的劲头。现在的问题在于,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思想观念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主流思想、主流价值观的推广传播不像过去那样顺畅,给我们在政论文章中的讲道理带来不小的挑战。这就更需要我们拿出“论”不服人誓不休的劲头,针对新形势下受众接受特点,研究讲道理的规律和技巧,把我们所要阐述、所要宣示的道理讲好,努力驱除“塔西佗效应”的魔影,让受众对我们的理论、对我们的观点心悦诚服,深信不疑。
为此,政论的作者首先要对我们所讲的道理怀有充分的自信,坚信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植根于当代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最新成果,具有高度的真理性和权威性,是解释现实、理解现实、指导现实的科学理论,具有内在的征服人心的巨大力量。同时,在讲述道理时,要努力追求说理的深刻与透彻,抓住根本、揭示本质,把道理讲准、讲清、讲透、讲全,充分释放我们所秉持的理论内蕴的强大能量。此外,要遵从理论阐述的逻辑规则,无论证实还是证伪,都要保证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做到严谨周密、无疏无漏,论据充足、论证合理,无懈可击、不可辩驳,不仅服人于口,而且服人于心。刘新如的政论实践已经说明,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理论真懂真信,并且善讲会讲,我们的政论一定会“走心”——赢得受众之心的。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