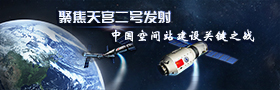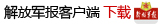编者按
这是一篇旧文,作者写于2014年7月致远舰复制舰下胎合拢之际。
当今天我们通过央视的全景直播,看到真实的致远舰那些锈迹斑斑的遗物打捞出水之时,关于那场战争那些军人的记忆,再度涌上心头。
东经124度9分37秒,北纬39度51分13秒。辽宁丹东一艘复制舰的诞生处,距其原型舰的沉没地仅30多公里。
相隔120年的两舰,都叫“致远号”。
关于这艘北洋水师航速最快的战舰,“百度百科”是这样记录的: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中,激战5小时弹尽且受重创后,管带(清朝军事官职)邓世昌欲冲撞日舰吉野与之同归于尽,但被日舰击沉,同舰官兵246人同殉职,邓与其爱舰同沉,全舰仅7人获救。
两个星期前,我在丹东见证了“致远号”纪念舰的下胎合拢仪式,也目睹了与致远同沉于大东沟的“超勇号”疑似残骸。作家萨苏这样描述后者几月前从淤泥里重现天日的一瞬:“钢板一片银白,几分钟后即锈迹斑斑,等待了120年的容颜在你面前迅速老去。”
一边是正在打造中的簇新钢铁,一边是沉睡海底的经年残片,锁于其间的120年岁月仿佛千山万水而又相去咫尺,令人不胜唏嘘。
今天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年。对那场战争的追问至今未歇,战败原因的探究由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思想文化而及军队管理体制、作战思想、训练方式和腐败胆怯之弊,不一而足。以北洋水师为代表的甲午军人在长留英雄浩气的同时,也承受了百年责难,命运一如致远舰悲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功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战争结局取决于大势必然也有天时偶然,但军人的担当却无法随历史风烟而散。
勿忘,甲午军人是中国第一批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并试图用西方科学技术强军强国的先行者。
环太平洋联合军演、亚丁湾护航,中国军队今日参与国际交流的常态,在百年前不可想象。消极者抚夷、偏激者鄙夷、无奈者和夷、积极者师夷,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不一,洋务运动则将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提升至新境。
1877年,中国海军首次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赴西方深造,多人进入英国地中海舰队实习,获得“未逊欧西诸将之品学”盛誉。1880年起,中国军人几次远赴英德,学习、验收并将清政府订购的战舰驾驶回国。至此,中国人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而是开始注视外部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
在萨苏看来,他们朝气蓬勃,是“带着微笑”、而不是“算计与仇恨”与西方交流的。
中国首任出使英国公使郭嵩焘在日记里写下了军事留学生们研习一幕:“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授,受益尤多。”留法博士马建忠如此表达正视中西方差异之心:“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
甚至有人与老外谈起了恋爱——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舰的年轻军官池仲佑与英国女子“意腻”(Annie Fenwick)。“黯然魂销,不忍长辞。匆匆一别,再晤何期?”惜别时,池仲佑拜托女孩代为照看病逝同僚的坟墓。2012年,一位名叫邓新力的中国记者拜访英国纽卡斯尔,犹见中国水兵墓前黄花依依。那是一种送给“永远不能还乡人”的花。
于风雨飘摇中走出国门的中国军人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近半数者生命止于甲午一役。
勿忘,甲午军人是中国推进近代国防转型、从全新高度审视海洋与海权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