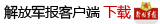2017年2月12日,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孙继炼与曾接受资助的红瑶姑娘代鲜花在展板上发现了18年前的合影。时光飞逝,子弟兵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教育事业的关爱却没有变。
特殊的亲人,难忘的身影
“他们就像我们的亲人,他们的心比金子贵”
“我是谁?我是妈妈的孩子,也是‘武警红瑶女童班’的孩子。”
“女童班”已成为代芸绕不过去的身份标签。绕不过去,是因为自己割舍不了。这位第二届女童班学生,如今已从大山走出来,在柳州这个城市扎根。
“说起党、说起军队,别人觉得远,觉得大,但在我心里,就是像何方礼伯伯一样的亲人。”代芸说,“他们就像我们的亲人,他们的心比金子贵。”
1992年,何方礼还是武警广西融水县中队的一名战士。他坚持把自己每月21元的津贴分作3份,8元寄给妹妹当学费,8元寄给红瑶女童班的学生,5元留给自己。在他的影响下,少抽一包烟、少喝一瓶水、捐助几元钱……逐渐成为一茬茬官兵的自觉行动。他们省吃俭用,持续不断给孩子们寄来学费、衣物和学习用品。
然而,要改变一个民族的观念谈何容易,刚刚走进学校的红瑶女童中间不断有人辍学。
“一个也不能少!”何方礼和战友们走村访寨、逐门逐户做村民思想工作。从此,一身橄榄绿,印在很多红瑶女童的心头——
崎岖山路,记住了那个背电视机的身影。那时候,大瑶山里没有信号,更没有电视,为了让瑶族人见识外面的世界,何方礼就用背囊背着电视机和卫星接收器,奔波在一个又一个村寨里。看着电视机前一张张惊奇兴奋的脸,何方礼幸福极了。那一刻,连续六七个小时山路跋涉所带来的疲惫一扫而光。
田间地头,记住了那个扛锄头的身影。为了说服家长让女儿上学,何方礼扛着锄头跟着乡亲到地里干活。人家施肥,他帮着施肥;人家锄草,他帮着锄草;人家一身汗,他也一身汗。
弯弯河道,记住了那个背着孩子的身影。上学路上,要经过河道、小桥、深山的女孩们不觉得害怕,因为何方礼和战友们经常会走在前面、护在左右。要是碰上大雨,上学的路被河水淹没,他们就一个个背着孩子上学……
那是一个周末。为了继续劝说一户人家让孩子上学,何方礼冒着暴雨深一脚浅一脚赶往大山深处的瑶寨。他一进门,女娃“哇”的一声扑向他的怀里,泪水挂在红红的脸上。望着浑身泥水的何方礼,孩子的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你这是何苦呢,咱这里的女娃从不上学。”“那是因为穷。”何方礼动情地说,“现在政府鼓励咱们红瑶女读书,就是要从根子上脱贫啊!她们长大成家后,还可以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认字,咱这瑶寨里也要飞出‘金凤凰’……”他们一直说到深夜,何方礼没有走,就住在他家堆放粮食的阁楼上。
第二天一早,何方礼走在下山的小路上,看到前方路两旁,女娃和她的妈妈在割草——她们是怕杂草荆棘上的雨水打湿他的衣服。女娃高兴地向他挥着小手说:“我明天就来上学!”看着眼前这一幕,何方礼的眼睛湿润了:多好的红瑶乡亲啊!
就这样,一个个辍学的孩子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教室。
今年元宵节,听闻已是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政委的何方礼又来红瑶女童班,早已从女童班毕业的一届届学生早早起来,穿上只有节日才穿的盛装,从大山深处四面八方赶来。她们拿出自家酿的米酒和油茶、自己做的手抓饭、自家养的土鸡、自家熏的腊肉,招待她们心中特殊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