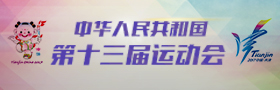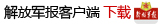关注天津全运会男篮比赛的球迷们发现,周琦“回到”了辽宁队、刘炜又成了上海选手、孟达重披江苏战袍、赵岩昊甚至成了天津青年队的一员……在CBA联赛各为其主的队员们纷纷“回归”或“转会”,成了全运会上一道独特的“临时工”风景。
其实这并非本届全运会的“专利”,过去几届全运会,CBA选手回到各种不同“母队”打球屡见不鲜,甚至还出现了巴特尔在三届全运会分别代表北京、山东、辽宁出战的“奇景”。当然,这也不是篮球项目的“专利”,只是因为职业联赛放开转会市场,而运动员们又大部分都属于各地体育局,在转会之初往往就有必须回来打全运会的协议,所以才显得人数众多。其实,放眼全运历史,几乎每个项目都有“临时工”的身影,这都源于全运会的运动员交流机制。
从1997年八运会起,全运会开始实行运动员注册制,为大范围人才流动打开了大门,八运会通过协议、转会流动的有800名运动员,创造了全运会人才流动的新高。再四年以后的九运会,人才交流更为频繁,一些规则漏洞和弊端也逐渐暴露。此后的三届全运会,国家体育总局对交流办法一再修订,十二运会时更是放出必须提前三年注册的“大招”。这些举措的推出,也令“临时工”现象有所降温。
客观来说,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希望有利于人才流动合理、有序、公开,让更多的运动员能有参加大赛的机会。例如本届全运会上,新疆女子重剑队就来自击剑大省江苏,在江苏队拥有许安琪等名将的情况下,小将许诺、戴莺等要想登上全运舞台并不容易,但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她们通过代表新疆队获得了机会,结果19岁的许诺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打进了四强,戴莺也打进了八强。
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代表团对金牌过于追逐,过去二十年里这一政策频遭诟病。十运会上,柔道奥运冠军孙福明不战而倒的“让赛”令舆论哗然,这也直接促使国家体育总局对解放军和地方双计分办法进行修订。在上届全运会上,连续三届代表三个单位参赛的巴特尔,高尔夫赛场上的众多“异地”职业选手也令不少人质疑这一政策变成了“人口贩卖”。
所幸,一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对交流政策不断调整,其目的无一例外地是为了打击急功近利的金牌政绩观。一位地方队教练告诉记者,以前很多交流就是“一锤子买卖”,“来了就是为了这届拿块牌,至于能不能带动这个项目的发展提高,根本没人关心”。
另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八运会开始的“东道主效应”,连续四届全运会,东道主都位居金牌榜首,这固然和几位东道主深厚的体育底蕴分不开,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交流甚至“买人”提升成绩也是东道主能稳居头名的重要原因。
但从上届全运会开始,这一“规律”终于被打破,这其中,对交流政策的重大改革不可忽视,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短期效应”式的人才流动。本届全运会取消金牌榜排位,更是从源头上淡化金牌意识的创举,很多老记者都发现,全运会上的“临时工”明显少了。
本届全运会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一些改革举措也令“临时工”变少了。马术场地障碍个人赛卫冕冠军朱美美就曾经是个“临时工”,上届全运会她代表北京队,本届全运会允许华人华侨以及达标的运动员参加部分项目比赛,朱美美以个人身份报名参赛,“临时工”成了“个体户”,比赛的精彩一点没少。
另一方面,本届全运会鼓励4人以下(含4人)项目跨单位组队参赛。乍一看这会催生更多“临时工”,但此“临时”非彼“临时”,很多队伍都是国家队组合,对他们而言如果拆散了回到省队才更像“临时工”。跨单位组队在赛艇项目上非常普遍,多支组合队伍获得冠军,在夺得冠军的湖南选手张亮看来,赛艇对技战术配合要求较高,如果国家队组合在全运会时拆散,之后将再度经历磨合期,而在全运会上与老搭档组合,不仅保证了配合的延续性,也能在实战中提升水平,更符合“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思路。
中国赛艇协会主席刘爱杰也说:“跨单位组合从备战、提高水平的角度来讲,它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高水平的团队。整体来说,这样有利于提高团队竞技水平。”
实际上,无论是运动员交流还是跨单位组赛,其本意都是为了打破地区壁垒和藩篱,鼓励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提高全运会的竞技水平和观赏性,进而推动项目在各地的发展,提高项目的整体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键还在于顶层设计上要不断完善改进,具体操作上不要把“好经”念歪了。
对各地而言,要提高某项运动在一地的发展水平,靠引进少数高水平运动员参加一次全运会显然不够,引进高水平教练、先进科学的训练办法、建立后备人才培养机制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以江苏女排为例,三年前他们请来蔡斌当主教练,三年间涌现了张常宁、龚翔宇等一批新星,不仅在今年勇夺联赛冠军和全运会冠军,张常宁、龚翔宇还成为国家队主力,刁琳宇、王辰玥也入选了即将开战的女排大冠军杯。
假如大家都有这样沉下心去抓后备人才的劲头,中国体育何愁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