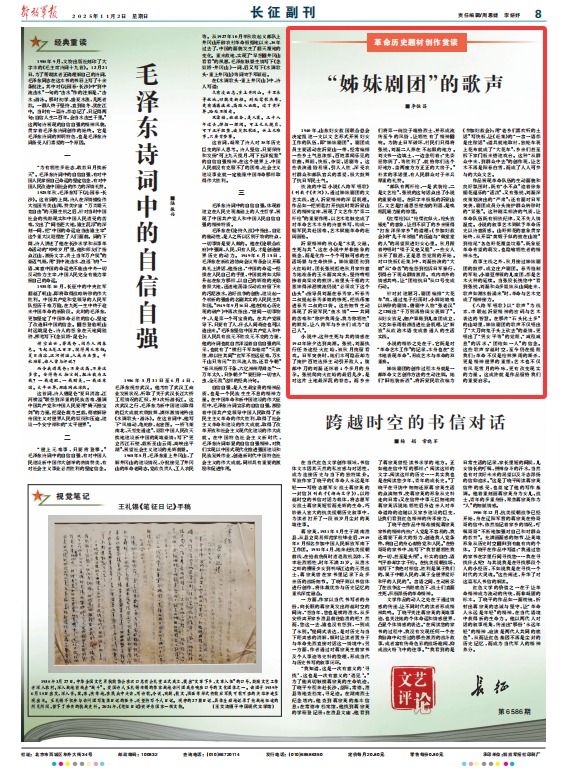“姊妹剧团”的歌声
■李恒昌
1940年,山东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决定组建一支以文艺形式开展妇女工作的队伍,即“姊妹剧团”。剧团成员主要活动在沂蒙山一带,经常编排一些乡土气息浓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舞蹈、快板、杂耍、话剧等。这些表演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深受农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喜爱,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
铁流的中篇小说《八路军唱歌》(刊载于《黄河》),通过姊妹剧团的文艺实践,进入沂蒙精神的深层肌理。作品如一把钥匙打开抗战时期沂蒙山区的精神宝库,展现了文艺作为“第二杆枪”的重要作用,以艺术笔触完成了对革命艺术本身的诗意书写,构成一幅军民共赴国难、艺术赋能革命的壮阔画卷。
沂蒙精神的核心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在小说中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作一个个可触可感的生活场景与生命抉择。姊妹剧团初到火红峪时,团长张锐拒绝秋月家特意为她准备的玉米面窝窝头,坚持啃咽掺着高粱皮的煎饼,被里头干瘪的大葱辣得涕泪横流仍说“必须攻下这个山头”;指导员刘磊在春秀家,听春秀二叔提起春秀爹娘的惨死,把钱币塞进春秀二叔的口袋。这些细节生动再现了沂蒙军民“鱼水情”——共同的苦难和“你护我周全,我为你牺牲”的默契,让八路军与乡亲们成为“自己人”。
小说中,这种生死与共的情感在1942年除夕达到高潮。张锐、刘磊执行任务途经火红峪,被秋月挽留看戏。日军突袭时,她们本可隐蔽却为了掩护百姓选择主动引开敌人。腹部中刀的刘磊还怀着4个多月的身孕。张锐爬向火红峪的最后几步,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而乡亲们将第一碗饺子端给烈士,并形成流传至今的风俗,让牺牲有了精神回响。为防止日军破坏,村民们只得将张锐、刘磊二人葬在不起眼的地方。刘支书一边填土,一边念叨着:“先委屈你俩了,等胜利了,就给你们选个好地方,盖两座方方正正的大房子。”朴素的承诺里,有人民群众对子弟兵厚重的礼赞。
“部队有两杆枪,一是武装枪,二是文艺枪”,张锐的这句话点出了小说的重要命题。在识字率极低的沂蒙山区,文艺是打通思想壁垒的利器,是唤醒沉睡力量的惊雷。
《红缨枪》以“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的意象,让目不识丁的乡亲懂得“打东洋保家乡”的道理;《参加妇救会》将“几千年锁链”的压迫与“做堂堂的人”的渴望照进妇女心里。秋月跟着哼唱时“嗓子又亮又脆”,一些女人抹开了眼泪,正是思想觉醒的开始。对口快板《赶集》中,刘磊扮演的“大娘”从“命苦”的抱怨到控诉日军暴行,引得台下观众群情激昂。戏内戏外的情感共鸣,让“团结抗日”从口号变成行动。
针对封建陋习,剧团编排“大花车”戏,通过鬼子扫荡时,小脚姑娘难以转移的剧情,借剧中人物“张老汉”之口喊出“千万别再给闺女裹脚了”。从妇女放足、佃户算账到儿童团成立,文艺如春雨般渗透进社会肌理,让“解放”从政治术语变成普通人的生活实践。
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既是对“革命艺术工作”的记录,本身也在“艺术地表现革命”,形成艺术与革命的双重奏。
姊妹剧团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部革命文艺创作方法的生动注脚。她们“旧瓶装新酒”,将沂蒙民歌改编为《参加妇救会》;用“老乡们喜欢听的土话”写快板,让《赶集》的“一言一语都是庄稼话”;道具就地取材,独轮车裹上花布就成了“大花车”,乡亲们甚至拆下家门板来搭建戏台。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观,让艺术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成了人人可参与的大众文艺。
作品展现革命队伍的生动面貌和良好氛围时,既有“小不点”追着徐东插花逗乐的“活泼”,又有张锐、刘磊深夜策划演出的“严肃”;还有面对日军突袭,剧团成员分头掩护群众转移时的“紧张”。这种刚柔相济的气质,让革命队伍既有钢铁纪律,又不失人情温度。小说的叙事艺术则赋予革命历史以诗意质感。山野鲜花的意象贯穿始终,从开篇“黄缎子似的披在山坡”到结尾“各色野花覆盖坟墓”,既象征革命希望的萌发,也隐喻牺牲者的精神永生。
故事主线之外,秋月接过姊妹剧团的鼓锣,成立庄户剧团。春秀缝制的军鞋、小崩豆带领的儿童团,都是艺术火种的延续。当张股长恍惚中“看到张锐、刘磊和众多姐妹从山间走来,歌声如潮水般涌来”时,革命与艺术完成了精神接力。
《八路军唱歌》以“歌声”为线索,串联起沂蒙精神的密码与艺术表达的智慧。在那片“石头比土多”的山坳里,姊妹剧团的歌声不仅唱出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豪情,更唱出了“男女平等”的觉醒、“减租减息”的诉求、“团结如一人”的信念。这些歌声穿越时空,至今仍在提醒我们:革命不仅是枪林弹雨的厮杀,更是精神世界的重塑;艺术也不仅有风花雪月的吟咏,更有改变现实的力量。这或许就是作品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