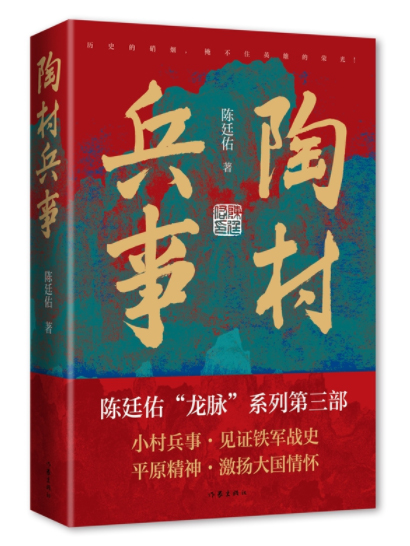
小说《陶村兵事》——
从“精神原乡”理解家国英雄
■季思含
作家陈廷佑创作小说《陶村兵事》(作家出版社)以冀中平原为背景,讲述了陶载石、陶砚瓦等两代陶村人,从抗日战场到和平年代,在同一支部队完成精神接力的故事。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描绘了那些有着“平原精神”基因的军人,在硝烟与和平交替中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图谱,展现了革命军人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结。
在叙事结构上,作者采用时空交叉与双线螺旋的手法,让过去与现在在叙事中不断碰撞,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比如两代陶村人入伍后到部队报到的情节安排,就突显了这种效果。第一代陶村军人陶载石、张鹭州完成新兵集训到部队报到时,一路凭借青纱帐巧妙躲过日本鬼子,隔着一条河望到了部队所在地——程院村。这时,他们突然发现“河的上游,大约150米处,支起一个军用帐篷,帐篷外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旁边两个人都挎着枪”。带队干部吴力耕低声说道:“不好,一定是敌人得到情报,准备袭击程院村,咱们必须破坏掉敌人的企图,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两个刚刚结束新兵集训的“新兵蛋子”,经历了他们人生第一次真枪实弹的战斗,并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这股敌人。
小说到这里,并没有接着叙述陶载石他们如何到部队报到,并受到部队的欢迎和表彰的,而是将笔锋转向几十年后的1972年,第二代陶村人——陶砚瓦等踏上从军征程的情节:“从闷罐车开动这一刻始,他们便把自己交给了军队,交给了国家,当然心里都有离开了家和亲人的丝丝伤感,更有对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的向往……闷罐车到了石家庄北站之后,终于下车吃饭了,主食是大米饭,就一个大锅菜,大伙儿吃了个‘沟满壕平’”。
不论是穿梭在青纱帐里,躲着日本鬼子的陶载石们,还是坐着闷罐车去报道的陶砚瓦们,都奔向同一个方向,奔向同一支部队——“八六一团”。这种“时空折叠”手法所营造的对比与跌宕效果,摆脱了线性叙事的单调乏味,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使得人物命运在关键节点上交汇碰撞,形成独特的艺术张力。
在人物塑造上,《陶村兵事》凸显军人精神与土地的血脉联结。书中的人物,他们像是从冀中平原的泥土里挖出的一株株庄稼——有根有须,还有迎风生长的倔强。如吴力耕,他是陶村小学教书先生,也是小说里第一个当兵的陶村人。他向3个学生道别时的一席话,指明他当兵是要抗日的:“东北没了,华北马上也快没了,蒋介石还是不抵抗!孩子们,半个中国都沦陷了!沦陷了!我要去抗战学院学习,是共产党办的,学完后去当兵,去抗日一线。”而彼时,日本人要来了,国民党籍的深县县长已经携家眷跑路了。
作者用反衬的手法,阐述了吴力耕的从军抗日的“根”是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激发出的民族存亡意识和保家卫国的紧迫感,充分展现冀中平原人民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由此,作者把这种情感作为一代代走进军营的陶村人精神的根,让它“串了根,发了芽”,使得小说中的人物轨迹清晰可见:吴力耕的3个学生,送别了老师后,光着脊梁跪在地上,相互在对方的背上刻下“精忠报国”4个字。作者充分利用这个典型的场景,使得陶村3位少年的形象更加具象化,同时也为他们最终走上抗日前线埋下伏笔。
《陶村兵事》中的很多人物,都带着平原人的印迹。正如陶村人在纪念村里抗日英雄时,用陶村式的谐音梗,把陶载石、张鹭洲、黎崇善的乳名串起:陶家狗,咬石头,黎家熊,拱碌碡。他们是在战火硝烟里成长起来的英雄,但在作者的笔下,他们还是带着泥土味的活脱脱的陶村人。
《陶村兵事》对深州方言的运用地道精妙,不仅增添了地域色彩,更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陶载石说的“中不中”里带着庄稼人的实在,战友间喊的“夜个黑介”(昨天晚上)透着生死与共的亲昵,就连陶母骂人的“你个憨货”,也裹着化不开的疼爱。
值得称道的是,作品中诗词的融入。全书融入46首诗词、书词、戏词等,体现了文学表达方式多样性的魅力。既有“此去山河远,犹闻麦穗香,报国非为誉,肝胆照乾坤”的悲壮果决,又有“沅溪才女万人知,素貌冻龄云水居”的典雅之韵;既有乡土文学的细腻之美,也有方言的鲜活之力。这种多元的语言运用,鲜活展现出他们是保家卫国的战士,也是眷恋土地的儿女。另一方面,书中许多地方通过“以诗言志”的方式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吴力耕离开陶村前所写“忍看平原遭酷屠,男儿不遣泪空枯。行将学业遗衰世,欲逐烽烟作武夫”表达了他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陶砚瓦在受挫时默写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暗示了他决心走出困境的韧性和豁达。
小说中反复提炼“宽平远志、正平守节、坦平无私、持平不争”的“平原精神”。这种精神是陶村先辈们在“国难当头,面对最残暴的敌人时呈现出的忠诚勇敢和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是他们“不打仗时好好种地,打仗时好好打仗”的朴素智慧;是新一代陶村军人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这种精神是他们“国之所需,我必往之”的担当,更是平原人乡土根脉、生死守护、信仰传承的交融。
小说结尾是“死而复生”的老英雄陶载石回陶村时的情景:“站立在四周的群众,没有动员,没有组织,陶村已然空巷,周围村庄的男女老少,也纷纷赶过来,观看陶村这百年不遇的盛况。之前他们听到了宣布,为了让老英雄不受打扰,对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要求,不许动嘴喧哗,只许动手鼓掌。”这是陶村人迎接老英雄回村的最高礼仪,是对老英雄最高的致敬方式,更是平原人骨子里那份信仰的接续:“咱村那个轴子,都当上营长了,北头二狗子家那个,从军校毕业当了参谋,文亮的儿子还参加了大阅兵哩,还有两个娃在朱日和也都转了士官,这样可以在部队上多干上几年哩,光荣着呢!”
又一代陶村人走进了我们的部队,我们将看到更多陶村军人的故事。陶村是他们的“精神原乡”。他们的精神也将在代代相传中,永远年轻,永远滚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