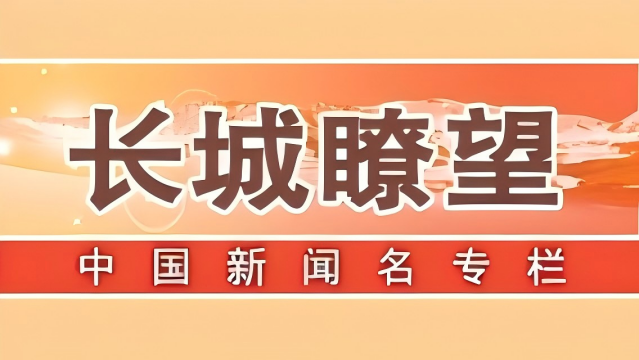风雨侵衣骨更硬
——评萧华回忆录《艰苦岁月》
■王雪
他既是一位战将,也是写下《长征组歌》的诗人。2025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再版的萧华回忆录《艰苦岁月》,为我们推开了一扇厚重的历史之门。这本书聚焦于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生动记叙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展现了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艰苦岁月》擅长以日常化语言叙事。比如毛泽东同志在兴国时叮嘱当地乡干部:村子里有座小桥坏了,要修好,不然小孩子上学要跌倒的。时隔几个月之后,毛泽东同志还问到瑞金去的兴国县长冈乡干部:小桥修好了没有?周恩来同志在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时跟青年们一起唱歌,一起登台演出,“在此起彼伏的掌声、笑声和叫好声中,分不清哪是演员,哪是观众,哪是首长,哪是战士……”作品通过生动的事例让读者深刻体会到群众路线的内涵,以及如何根据青年的特质开展工作,使革命队伍充满活力。《艰苦岁月》以平易近人的叙述方式,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与官兵、群众之间的深厚情感纽带。这些日常化的语言,不仅拉近了历史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也让宏大的革命叙事变得亲切可感。
作者笔下描绘的军事行动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如山东根据地通过被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的武工队、游击队等短小精悍的部队有力打击敌人;横跨渤海进军东北时,第一次实现以木船渡海的战略决策,靠的是顽强的斗志和毅力、鲜血和生命,靠的是全体指战员的一片“碧血丹心”。这种兼具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的叙写,正如《长征组歌》中“风雨侵衣骨更硬”的诗句,既是战斗实录,亦是精神宣言。
《艰苦岁月》用朴实的笔触勾勒出革命队伍中那些令人难忘的身影。这些人物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动态交融的革命共同体。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首长不仅在战场上指挥若定,还主动为宣传队导演话剧,与战士们同台演出,“兵演兵,将演将”,让革命的精神在文艺活动中传递。这些鲜活的面孔,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共同编织起热烈的革命情谊。
在《挺进冀鲁边》这篇文章中,萧华描写了1938年冀鲁边区发生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狡猾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是一个顽固派,企图以“明升暗降”的伎俩撤换抗日县长牟宜之。这一天,沈鸿烈带着随从驱车闯入乐陵,威逼利诱牟宜之离任。话音未落,县府外已掀起震天声浪:“维护真心抗战的牟县长!”“反对破坏抗战的汉奸行为!”成千上万的百姓举着彩旗涌向街头,老人拄着拐杖,妇女抱着婴孩,青年攥紧拳头,将县府围得水泄不通。沈鸿烈慌忙将牟宜之拽上汽车,试图强行带走。不料车刚出南门,更大的阵仗在等着他——公路两旁人潮如海,两万多名百姓席地而坐,用身体封死去路。有人拍打车窗质问:“牟县长带着我们打鬼子,凭啥赶他走?”有人索性躺在车轮前高喊:“想带走牟县长,先从我们身上轧过去!”沈鸿烈急得满头大汗,可他哪里知道,这场“护县印”的戏码本就是我抗日军民合演的杰作。最终,沈鸿烈只得灰溜溜交出牟宜之,在百姓的怒视中仓皇逃离。当政权争夺化作街头巷尾的民心较量,当“军民一家”从口号落地为并肩而坐的身躯,革命的火种便真正扎根在了这片滚烫的土地上。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艰苦岁月》对革命主题的阐释超越了军事胜利的表层,深入至精神信仰的维度。书中对艰苦环境的描写极具象征意义:在井冈山,朱德饿了的时候,就把锅巴、炒米用白开水泡一泡来充饥;萧华夫妇在渡海出兵东北的渔船上,看着准备好的火烧和咸菜,高高兴兴地出海。这种“苦中作乐”并非对苦难的浪漫化,而是揭示了革命者以精神超越物质的生存哲学。这其中的核心命题是个体如何将生命融入历史进程。萧华在书中反复强调“忠诚”与“信仰”的力量:他因毛泽东的知遇之恩而“一生追随”;因周恩来的关怀而“誓死捍卫青年工作”;在被疾病折磨的晚年,他伏榻撰写《艰苦岁月》,为的是能给广大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真实的教材。这种精神传承在《长征组歌》中达到高潮——通过诗歌与音乐,长征从历史事件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的符号。
因此,《艰苦岁月》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提供了一种革命叙事的重要范式。它通过个体经验的真实性、人物关系的丰富性、革命智慧的多维性,构建起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桥梁。在当代语境下,这种书写方式提醒我们:对革命历史的书写,很重要的是体现革命精神的光芒和红色基因的传承。“一身换得百花开,赤血丹心映日来”。《艰苦岁月》的魅力必将在时光流逝中,更加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