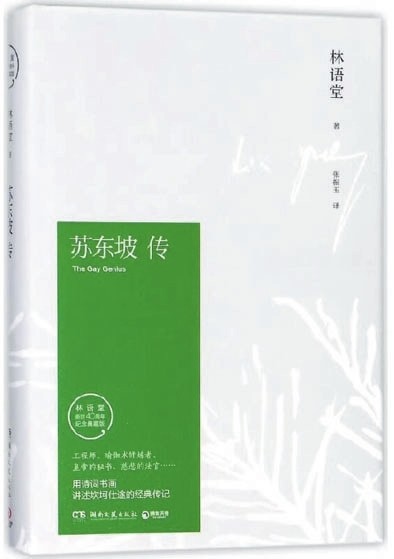
苏东坡是个什么样的人?
——品读有关苏东坡的几本传记和论著
■陈永刚
大约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
一提到苏东坡,不少人会想起林语堂《苏东坡传》序言中的一段话:“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尽管在林语堂看来,“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但这些重重叠叠的身份已然展现了苏东坡独特的人格魅力。
要想真正了解苏东坡,第一手的材料当然是他留下的诗词、散文和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同时也可参考他同时代的朋友、弟子有关他的笔记、著述,以及后世学者关于他的研究论著。不过,如果只是喜爱苏东坡的普通读者,也可以先从阅读当代人撰写的苏东坡的传记入门,有兴趣再逐步深入研究。近两年,在工作之余,我集中阅读了几位当代学者和作家撰写的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和论著,包括林语堂《苏东坡传》、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王水照与崔铭《苏轼传》、莫砺锋《漫话东坡》、张炜《斑斓志》、徐棻《苏东坡》以及康震《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从形式上看,这些作品既有人物传记,也有研究随笔,还有长篇历史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由于各位作者文学素养、研究志趣和情感倾向的不同,他们各抒己见,给我们呈现的苏东坡形象也各有侧重和不同,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苏东坡的理解,也让我体会到苏东坡的丰富性。
苏东坡享年66岁,如果从他考中进士算起,在45年时间里,创作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写下4800多篇文章,此外还兼工书法、绘画等,这无疑展现了苏东坡超凡的创造力。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坡并不是一个职业文学家或艺术家,他的正经工作是“做官”,这就意味着他实际上要干很多政事,写文章大多数时候只是“余事”,但这并未妨碍苏东坡的艺术创造性。康震说,苏东坡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在诗歌创作上,他是宋代诗风的代表性诗人;在词创作上,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散文创作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书法创作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是北宋书法风韵的代表;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北宋“蜀学”的中坚。在绘画、宗教、饮食等方面,苏东坡也有很深的学问。仔细算来,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还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涉足这么多的艺术和学术门类,并且在各个领域中都展现出杰出的才华。
毫无疑问,苏东坡的才华在他那个时代是举世无双的,不过,比起才华,今人更加喜爱的则是他被才华重重包裹的心灵和人格魅力。

愉快的天才
在当代出版的各种苏东坡的传记中,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本。这本传记是林语堂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给外国人看的,后来翻译成中文,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发行。英文版的书名叫The Gay Genius,直译成中文就是“一位愉快的天才”。这个书名很切合该书内容,也是苏东坡留给人们的最直观印象。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贯穿全书,他在序言中坦言:“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在书末,他又写道:“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苏东坡确实是一个“愉快的天才”,他一生遭受了那么多的坎坷和折磨,但他始终乐观对待生活。他常常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品赏自己的苦难,并用“开玩笑”的方式加以消解。他被贬黄州时,生活窘迫,东门外有一块人们都不要的瘦瘠坡地,他跟长官讨来,开垦种植,并自号“东坡居士”。古人常常自命雅号,表达一种生命的寄托,态度比较庄重,苏东坡却寄庄重于诙谐。他在东坡过着“躬耕”生活,还创制美食“东坡肉”,写下《猪肉颂》,把清贫日子改造成人人羡慕的诗意生活。这就是苏东坡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厚重的精神文化遗产。他面对困境不抱怨、不沉沦,而是以“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乐观心态积极应对。晚年苏东坡自流放地海南渡海北归,苦难结束,兴奋想必是意中常情,但苏东坡以玩赏的口吻说,这几年的海岛生活,实属“兹游奇绝冠平生”。人生的苦难,被他视为不可多得的高峰体验,这真是常人不易有的达观视角。
林语堂是现代文学史上提倡幽默文学的著名作家,他的文笔欢快轻松,其天性中似乎拥有与苏东坡相近的性质,宜乎其喜爱苏东坡。但是若把苏东坡全看成乐天派,也会引起后来人的不满。在这不满的人中,台湾学者李一冰是代表性人物。李先生耗时数年写了一部规模更宏大的苏轼传记,精心描绘了他自己心目中的苏东坡形象。
坎坷无尽的英雄
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是一部非常厚重,充满悲怆与力量的作品。此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1983年由台湾联经首次出版,深受好评。2006年,该书在大陆出版。202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新增订版,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张辉诚《寻找李一冰》、李雍《父亲与〈苏东坡新传》两篇介绍作者生平事迹的文章。
李一冰,原名李振华,以“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取笔名“李一冰”,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1947年到台湾。1967年,因政治冤案入狱4年,1971年出狱。在狱中,他凭记忆默诵苏东坡诗词以自遣,出狱后更以苏东坡为精神支柱,耗时8年写成《苏东坡新传》。了解一下李一冰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就可知道该书实为一部“发愤”之作。
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是浪漫化的,而李一冰的写作扎根于翔实的史料,考证巨细无遗,更具史家的严谨。全书以编年体形式将苏东坡的诗词、宋人的笔记嵌入具体历史事件,形成“以诗证史,以史释诗”的双向互动,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
该书对苏东坡贬谪生涯的刻画尤为深刻。张辉诚在《寻找李一冰》中说,李一冰不像林语堂,他看到的苏东坡是“狱中狼狈至极的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坚韧的东坡,他更从东坡一生看到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看到一肚子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换句话说,李一冰写苏东坡,实则是在写自己,他借东坡的行止来浇自己的块垒。
苏东坡一生坎坷很多,除了三次贬谪遭遇,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挫折,长时间的人生挫折与逆境,没有打倒他。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时都迸发出了独特的人格光芒。他晚年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表面看是自嘲,其实是对功利主义的世俗人生价值观的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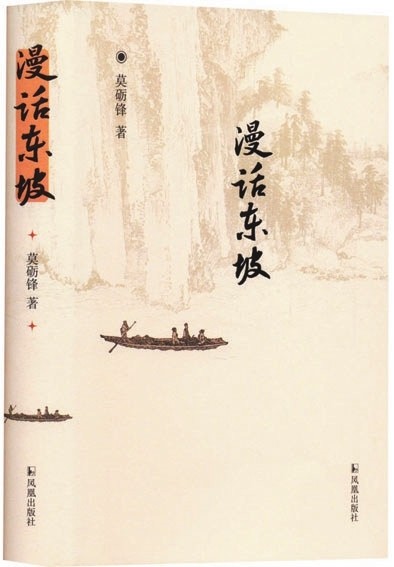
不合时宜的政治家
苏东坡,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仕途辉煌的时候,在朝廷,他担任中书舍人,做翰林学士,执掌皇帝制诰写作,他的职位离宰相仅一步之遥;此外他还兼任侍读,做皇帝的老师。在地方,他做过密州、徐州、登州、杭州等重要州府的“一把手”,深悉民情,政绩显著。与辉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也曾进过御史台的大牢,还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等荒瘠之地。其中儋州更是当时远州的极限,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苏东坡的一生与政治息息相关,其人生起伏不过是政治境遇否泰变化的外现。因此,政治生活是今人书写苏东坡人生的重要内容。研读各家论著,我们也不难发现,苏东坡的政治境遇与他一贯秉持的政治理念和做人准则息息相关,简而言之,他就是敢于讲真话。
北宋中后期,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新旧党争,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矛盾。“新党”以王安石为首,主张变法,推行新政。“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维护旧的规章制度。两派势不两立,针锋相对。那么,苏东坡站哪一派呢? 过去,很多人简单地认为苏东坡是个反对“变法革新”的保守派,并将此视为苏东坡的政治污点。
莫砺锋在《漫话东坡》一书中对此做了新的论述。他认为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问题上的态度其实是有点中立的,他既看到了新法的种种缺点,也看到了其中某些合理性的部分。川剧著名编剧徐棻在其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中,也对苏东坡历来遭人诟病的“反对变法”问题做了自己的诠释,她认为苏东坡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反对变法中的部分政策,他对免役法中的一些改革举措就持肯定态度。徐老师这本书虽然是历史小说,带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她曾讲述她的创作基本遵循了“历史事件件件皆有出处”的原则,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书内核还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是可信的。在变法问题上,苏东坡确实是个实事求是派。他发表意见完全从事实出发,不会见风使舵。所以,当王安石雷厉风行实施新政,为此甚至不惜采取排除异己的手段时,苏东坡是反对的,但他也看到了朝廷沉重的负担需要通过革新来解决。事实证明,王安石的新法由于实施得太急,有些尚未充分论证就在全国推行,在部分领域确实制造了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因此,苏东坡反对变法中的一刀切、急于求成,主张慎重,不可操之过急,则是比较务实、理性的。
在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去世后,在高太后的干预下,“旧党”上台,司马光当了宰相,苏东坡也受到重用,回到朝廷担任要职。在反对新法这件事情上,苏东坡、司马光共进退,应该是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但当他看到司马光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新法全部推翻时,他又站出来反对。他说,新法中有些措施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执行了多年,老百姓都习惯了,全部纠正过来,反而不稳妥。幸亏司马光人品好,虽然意见不合,他并没有打击苏东坡。但是一年后,司马光去世了,他的亲信把苏东坡视为“眼中钉”,苏东坡在朝廷无法容身,只好主动申请去地方州府任职。这就是苏东坡,一个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政治家。
李一冰在其《苏东坡新传》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此外,他还特别指出,苏东坡是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利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由此,“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是非心,而又忍不住要说真话的人,尤其不适于参与现实政治。否则,遭逢祸患,几乎是势所必至的命运”。苏东坡一生,祸患不断,原因即在于此。
常有陪伴的普通人
苏东坡富有生活情趣,他善于发现并创造生活的趣味。这表现在他与各种人群平等而友善的交往当中。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他充分享受着生活的趣味与快乐,也让与之交往的人感受到趣味与快乐。
张炜的《斑斓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苏东坡传记,而是讨论苏东坡待人接物思想的随笔。全书分成七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下有若干个话题,每个话题的写作短小精炼,展开苏东坡人生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度挖掘。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关于陪伴的话题。张炜说:“友人、兄弟、爱人、山水、同僚,他的一生常有结伴。由此看,如果说他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还不如说是一个难以忍受孤独的人。”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苏轼与弟弟苏辙一生的陪伴。苏辙比苏轼小三岁。他们同时进士及第,同时考中制科;进入政坛后又经历了命运相系的宦海沉浮,最后一起被贬到荒远的岭南,他们是一对真正的“难兄难弟”。他们性格不同,但一直保持着最亲密的手足之情。哥哥到远方赴任,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弟弟远去,兄长也一定要陪伴。分在两地,他们就为对方写一首长诗。熙宁九年的中秋之夜,思弟心切的苏轼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中秋词《水调歌头》,他责问天上的明月为何偏要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变圆。张炜在书中感慨道:“兄弟二人遥遥相隔,共邀一轮明月的情景,真是旷世之思,世上没有一首中秋词可以胜过它。”
除了弟弟,他与父亲、妻妾、儿子也是投契的友伴,对待门生、同僚,也是情谊深重。他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离任时朋友们送他到湖州,聚在一起欢饮数日。他离开黄州,一些朋友一直陪伴他到了武昌,直到他再三劝阻,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地返回。
最后,张炜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类似的陪伴需要多少时间? 耽搁多少事情?”在现代社会,高新科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相互联系更为便捷、紧密,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空间,但我们好像并未因此变得更加从容舒展,我们和亲友间的陪伴似乎也没有变得更多更密。苏东坡在山迢水远、消息难通的古代,以对友人、兄弟、爱人、同僚的赤诚之心,告诉我们,山高水长从来都是借口,真正的陪伴是心中时时不断的牵挂,真正的亲情、友情是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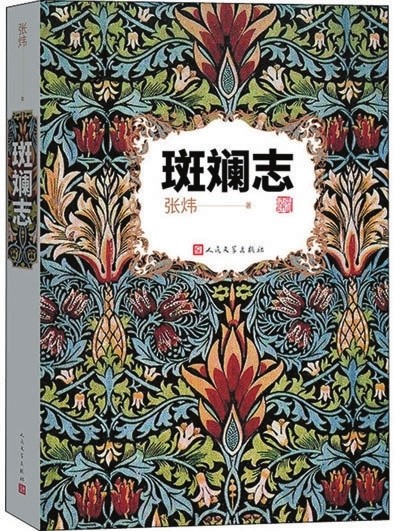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偶像
中国传统士大夫一直在追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正道,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人格。在这方面,苏东坡为后人作出了光辉榜样。
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认为,苏东坡正是在仕途沉浮中获得了精神超越,并最终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倾慕的偶像。
《康震诗词课:苏东坡12讲》也以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亲和力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康震说,苏东坡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终其一生,无论遭遇多少坎坷委屈,都始终坚守对家国、百姓的责任,从不自我放弃,更不会摆烂躺平;不论面临多么艰危恶劣的环境,他始终敢于说实话、讲真话,从不虚与委蛇,更不会朝三暮四、落井下石。在苏东坡的身上,有李白超凡的神仙气,有杜甫执着的忠义气,有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情怀,有白居易直言敢谏的批判精神。苏东坡的思想人格传承先贤、融汇各家而又自出机杼。
一直以来,“出与处”都是最让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纠结的问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很多人的处世方式,但是苏东坡却非如此,无论官职高低、境遇顺逆,他都始终心系百姓,在杭州修“苏堤”缓解水患,在徐州带领百姓抗洪,在儋州推广农业技术。其“民胞物与”的思想为后世知识分子树立了典范。
以上这几部论著,对苏东坡形象的刻画,有些内容颇为相近或重叠,有些则彼此不同。上述五个方面是我的一些粗浅感受,或许也是“盲人摸象”,不求全面系统,只求主观认可。研读这些论著,除了加深我对苏东坡的理解外,还带给我几点感悟和启示。
第一,“乌台诗案”开创了北宋“以言获罪”的恶劣先例,对北宋文化生态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是莫砺锋讲述“乌台诗案”时提出的重要观点。他认为,“‘乌台诗案’不仅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凶险的一场灾难,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使人谈虎色变的文字狱典型”。我们知道,“主文而谲谏”“诗可以怨”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精神,苏东坡却因此而获罪,“新党”把宋太祖制定的“不得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完全抛弃不顾,既是对诗歌传统的反动,也是对传统政治言路的破坏。故此莫砺锋先生感慨:“‘乌台诗案’开创了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恶劣风气。”事实证明,仅仅十年后,重新掌权的“旧党”也如法炮制,制造了打击“新党”人物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又过十多年,宋徽宗、蔡京等人变本加厉,竟然下诏销毁苏东坡及司马光等人的文集。北宋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遭受严重破坏,“乌台诗案”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第二,公道自在人心,是非自有公论。北宋时期由王安石推行新政引发的新旧党争,持续时间之长,危害程度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神宗年间的政治争论到徽宗年间的“元祐党籍碑”,党派之争由政事之争逐渐沦为个人恩怨的报复行为,让人十分痛心。章惇曾经是苏东坡的朋友,两人年轻时就认识,相交甚密,但自章氏成为“新党”骨干,执掌大权之后,他却一心要置苏氏兄弟于死地。苏辙在雷州时被逐出官舍,无地可居,只好向百姓借房,章惇竟要以“强夺民居”的罪名逮捕苏辙,还把房主抓来审问,幸亏有写得明明白白的租房文书,这才算作罢。宋徽宗上台后,以章惇曾反对自己承继大统,将其也贬至雷州。章惇也向百姓借房,当地百姓表示,从前苏公租住民房,章丞相几乎破了房主的家,所以现在对他也概不租用。这是多么大的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流放章惇的蔡京后来也被流放,流放地也在岭南,只是他还没能到达那里就饿死在路上了。据说是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路上没有人卖给他食物,也没有客栈让他住宿,所以,未到岭南,便在路途中冻饿而死。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第三,面对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我们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挫折、低谷甚至逆境,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态度对待它。苏东坡的一生,大起大落,曾经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从黄州的一个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可谓“火箭式”飞升;也曾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从一个三品大官一路被贬,还以戴罪官身安置在远州不得擅离,堪称“断崖式”跌落,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虽然备受挫折与打击,苏东坡从来没有被击倒。即便是在当时偏僻蛮荒的海南岛,他也依然笑对人生,苦中作乐。他的词“一蓑烟雨任平生”最能展现他的精神,这不是消沉,而是以从容的心态、坚定的信念面向未来。
我们知道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不妨现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苏东坡,我们民族的文化史会损失掉多少有价值的内容。正因有了苏东坡,我们民族的精神史才有了如此鲜活、有力的人格底色。苏东坡是历史的,更是现代的,也必将是永恒的。他坎坷但乐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关于他的话题还会继续。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