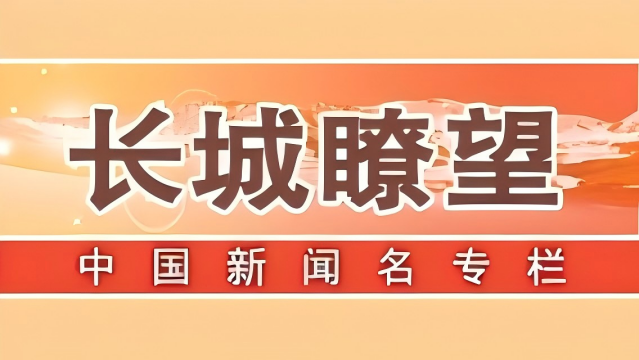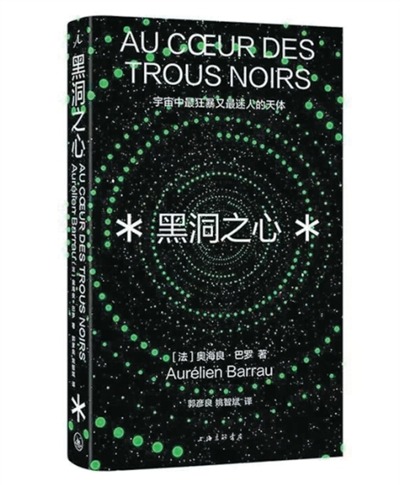
《黑洞之心》:
当我们抵达想象的边界
■熊建
人生很短,倏忽百年。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组成人体的那些粒子,什么夸克啦、胶子啦,其实和宇宙的年龄一样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咱们身体的年龄已经超过130亿岁了。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还是保守了,应该改成“常怀亿岁忧”。
抛开数字的差距,事实上,地面上的问题,人生的困惑,从天上找答案,从古至今、从中到外,都很流行。即便到了今天,天文学知识依然可以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思考的全新角度和维度。比如黑洞。
早在18世纪,英国的天文爱好者约翰·米歇尔和法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就已经预见了黑洞存在的可能性。从那之后,这个“‘看’不到的家伙”,就进入了人类的语言词库,影响着天文学、科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那么,该怎么理解黑洞呢?怎么看待它与我们的关系呢?阅读《黑洞之心》这本科普读物,就是很好的选择了。
本书作者奥海良·巴罗是法国物理学家,专业领域是黑洞、粒子天体物理和宇宙学,此外还是哲学博士。这样的学术背景,让他在进行黑洞科普时,并不漂浮在天上,而是时刻注意与人间的关联。换句话说,这本书,好比是黑洞与人的桥梁。研究黑洞、走近黑洞,与其说深入宇宙太远了,不如说离我们的人心更近了。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黑洞是“宇宙中最狂暴又最迷人的天体”。说它狂暴,是因为时空因为黑洞的存在而变得疯狂。物理学讲,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可以弯曲时空,而黑洞弯曲世界的程度之大,会让它永远是赢家,无人能拂逆它的力量。
说它迷人,是因为当我们深入探究黑洞之后,会领悟到很多醍醐灌顶的信息,比如光线如果沿着被黑洞严重弯曲的空间传输到观察者的眼中,我们会看见同一颗星星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位置上。这是颠覆常识的知识,也是让人“拈花一笑”的体验。
因此,要理解黑洞,必须抛弃中学物理课上学来的知识,但又不能真的抛弃,因为没有一二楼,怎么会有三四楼?所以,用超越来形容观察黑洞后产生的知识飞跃,更合适。而由此产生的颠覆性认知,更让人读后大有“霍然汗出”之感。
比如,书中大胆畅想在黑洞中旅行的场景。假设我们能跳入黑洞,抵达黑洞中心——所有坍缩并创造了黑洞的物质,都集中在黑洞中心的一点,那么,在这个无限小、密度无穷大的区域,在这个比原子还小、包含数十亿千克质量的点,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作者给出了他的答案,那就是时间的终点。当然,这是一个科学猜想,而且很难想象。这就是科学的魅力之一,它在不断扩展人类想象的边界。
不用担心看不下去,《黑洞之心》的出发点是科普,读者对象是大众。作者深知如何产生“阅读友好”的体验。比如他采取对话体,虚构了两个人物,一问一答间,把深奥的天文知识转化为日常的闲谈,没用一个数学公式,绝不繁复地论证,顶多用几个图表,帮助理解。这种“拉家常”的行文方式几千年来屡试不爽,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都是运用对话来传递道理的经典文本。
当我们合上书页,那宇宙深处的幽暗之心,并未远离。它曾是先贤笔下的玄思,如今是科学探索的边疆;它扭曲时空,却也照亮认知。我们这具由百亿年星尘汇聚的躯体,试图理解那时间的终点,这本就是一种壮丽的浪漫——在仰望那最狂暴的宇宙深渊时,我们反而找到了自身存在最深邃的回响。这,或许正是《黑洞之心》想要馈赠给我们的:一次在无限与永恒面前的顿悟,一粒在浩瀚中确认自身意义的、微小而坚定的尘埃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