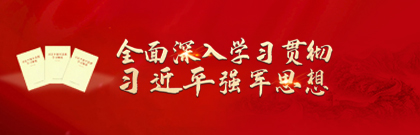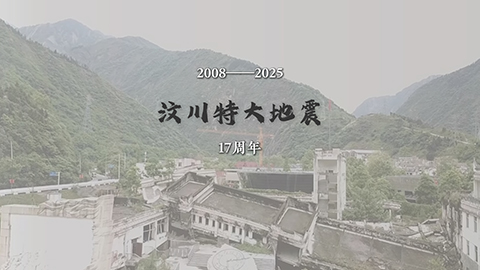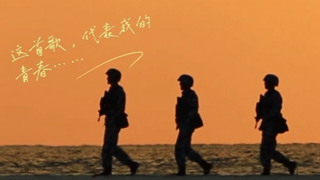用生命书写的无声誓言
■剑 钧
一
在武陵山东部的鄂西南,恩施的方家坝后山,群山环抱,云遮雾绕的山林之中,有一条曾经带血的山路,由100余级石阶组成。82年前的1941年,还差4天就满26岁的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戴着镣铐,迈上走向死亡的100余级台阶。凶残而阴险的刽子手,妄想用石阶来动摇何功伟的信仰。何功伟每上一级台阶,行刑者便追问:“回不回头?回头可免于一死。”他冷然一笑,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岂是区区100级石阶就可以动摇的?英雄昂首,头也不回地迈向了五道涧刑场,走完人生最后的100余级台阶,也放弃了100余次活下来的机会。
那100余级台阶,每登上一阶,就是一句共产党人的人生告白。我看着何功伟生前的照片,被这个泣血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那张照片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张很时尚的摄影,风华正茂的何功伟,一头浓发向上梳起,浓眉下,一双坚毅的大眼睛,闪烁着追求真理的目光。凝视照片,我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当年100余级石阶上,那个伟岸凛然的高大身影;联想起临刑之前,何功伟倾情写下那封催人泪下的家书。我在想:如果说,100余级石阶是何功伟慷慨赴死的英雄见证,那么,写给父亲的家书就是何功伟忠诚信仰的最后宣言。
那100余级台阶,每登上一阶,就是一行用生命书写的无声誓言。读烈士家书,我能感受到文字中散发出的浩然正气:“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这诗一样的语言,是何等悲壮,又是何等壮怀。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到岳飞蒙冤风波亭,尽忠报国;再到何功伟视死如归,含笑九泉……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无不以救国家于危难、解民众于倒悬为己任。幸有先贤的前赴后继、砥砺前行,华夏文明才得以延续五千年而经久不衰。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二
读烈士家书,我蓦然领悟到鲁迅先生的那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杰”的真实含义。何功伟身陷囹圄,自知来日不多,思亲的情怀愈发浓烈。家书开篇就说:“儿不肖,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计。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河山还我之日,即天伦叙乐之时。”我读到此处,眼睛是湿润的,分明看到了烈士内心那柔软的一面。他在家书中写道:“儿七岁失恃,大人抚之养之,教之育之,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恩山德海,未报万一。今后,亲老弟弱,侍养无人。不孝之罪,实无可逃。然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致不能事亲养老,终其天年,苦衷所在,良非得已。”他深爱自己的家乡,也深爱自己的亲人,但他意识到“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福祉,他别无选择,只能是死而后已。
犹记1940年初夏,日寇出动大批军队,从武汉进犯宜昌。中央决定将我党机关撤离宜昌。时任湘鄂西区委书记的何功伟临危受命,夜以继日地安排同志们分批撤往巴东和恩施。直到敌机投下燃烧弹,市内火光冲天,他才最后一个离开宜昌。“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忘餐,为当局所不谅。”此言可谓发自心声,也是对父亲的真情倾诉。何功伟到达恩施后,又被任命为中共鄂西特委书记,继续领导这一带的抗日斗争,足迹遍布城乡。时间到了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策动“皖南事变”,白色恐怖也蔓延到恩施地区。盘踞在鄂西的反动派进行了疯狂大搜捕。由于叛徒告密,何功伟于1941年1月20日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各种劝降伎俩,面对火烙铁、老虎凳等严刑拷问,何功伟无所畏惧,痛斥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反动派无计可施,就将何父接到了恩施,妄图以骨肉之情来软化他的革命意志。何功伟得知后就在家书中挥毫写道:“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
那100余级台阶,每登上一阶,就是一句对烈士家书的最好诠释。家书原稿被敌人搜走后,送到了国民党军官陈诚手上。陈诚看罢连声叹道:“我们国民党内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才!”他在原稿上写了“此人伟大”4字,并将家书扣压,并未寄出。我们看到的那封家书,是何父与儿子在监狱见面时,何功伟为保护父亲及家庭重写的。当时,陈诚为了诱降何功伟,许诺只要交出共产党组织名单,进省府当委员、秘书,上大学和出国留学等任他挑选。何功伟对之报以冷笑,让敌人无计可施。
那100余级台阶,每登上一阶,就是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英雄悲歌。“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突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几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家书字字血、声声泪,是何功伟慷慨悲壮之辞。想起当年,周恩来同志闻知“皖南事变”后,痛心疾首,曾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何功伟带镣长阶行,是在用鲜血和生命唤醒民众。“忠贞那(哪)惜头颅掷,含笑刑场典范留”,这是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何功伟的老战友钱瑛为他写下的诗句,深情讴歌烈士永存的英灵。
三
在恩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张母亲与孩子的照片,分别是何功伟的爱人许云和初生的爱子。这是一张妻子寄给丈夫的照片,但最终也没能送到何功伟手中。之前,狱中的何功伟曾先后给父亲和妻儿写过3封信,一封写给父亲的信被陈诚扣压了;一封写给妻儿的信,我无从知晓是否会收到;就是这封写给父亲的家书也是辗转一年多后,许云才含泪看到的。其实,那封信已远远超出了家书的范畴,让后来人读懂了先辈们牺牲与奋斗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100余级台阶可以作证,何功伟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的一腔热血浇开了漫山遍野的红杜鹃,他和无数先烈们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对此,长眠群山中的何功伟烈士早就预言到了。他在家书中写道:“胜利之路,纵极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不疑者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以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景。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而笑也。”
那100余级台阶可以作证,何功伟烈士的英灵,如今仍久久萦绕在崇山峻岭之上。每当清明之际,无数少年儿童会来这里拜谒先烈,和叔叔阿姨一道献上一束束鲜花。何功伟本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品学兼优,志向高远。他也曾有过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民生凋敝和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何功伟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是他毅然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从那一刻起,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也正是先辈的奋斗牺牲,才使我们的孩子们有了今天的幸福童年。
而今,当人们沿着这100余级台阶往上攀登的时候,头上云海茫茫,脚下林涛苍苍,登高远眺,可看万山红遍,可看层林尽染,但你可曾想到:那遍野的红花是怎么开的,那漫山的绿荫是怎么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