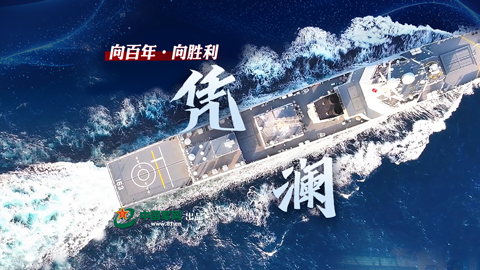我的“战地写作课”
■贾永
1981年5月,离国境线几公里的一座野战油库内,正在举办一期新闻短训班。战事来得突然,原本计划10天的培训提前到第6天结业。班上两个年轻的士兵,分别跟随步兵和炮兵参加了一场作战。两周之后,随步兵行动的小伙子牺牲在了战斗中,刚满19岁,名叫叶永宁;与炮兵部队一起行动的年轻人就是我。我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之路,就这样从战场上开始了。
那一年,我18岁。
叶永宁是在战斗最激烈的5月16日运送炮弹过程中牺牲的。躲过了连续飞来的3发炮弹——第四发,他却未能躲过。留在画夹中的速写和剪纸作品,成了他永远的绝笔。那时候边防部队营这一级还没有照相机,全靠叶永宁这样有些美术底子的战士用画笔记录战地生活。
也是在5月16日这一天,我和团政治处干事周杰前脚离开一处炮阵地,敌人的炮火急袭就毫无征兆地开始了。就在我东张西望的瞬间,忽听见头顶一阵刺耳的呼啸。周杰猛地把我扑倒在地……几乎在同时,一发炮弹在身后不远处爆炸,轰起的土石落了我们两人一身。好在当时只是轻伤,涂了些药水也就好了。
那天晚上,我蹲在前线猫耳洞内,借助手电筒的亮光,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战地新闻《亲人嘱托记心间,杀敌报国立新功》,刊登在1981年6月17日的《战士报》上。我当时写的两篇战地散文《神眼》《大炮上刺刀》,也被收入了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战地散文集中。也许,这就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1982年春节,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辗转送到了阵地上。打开一看,歪歪扭扭写着这样几个字:“儿,速寄一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母亲是一位几乎不识字的裁缝。看到这封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战友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急急跑到离阵地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带有两个耳朵的照片,连同刚收到的散文集寄回了家。直到几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这封来信的谜底。我的一位老乡,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根手指。老乡因伤退伍回到老家,很自然地去探望我的父母。听说我的战友从遥远的边防线回来,左邻右舍挤满了我家不大的房间。当人们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一不留神说了实话,摇着那只缺了小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每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待到他意识到说漏了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就白了。过了几天,家乡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可以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谣传的人。
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传的源头。一个月后,这源头还真让母亲找到了,居然是一户与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他们说得也似乎在理,你儿子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而你儿子一直在阵地上跑,能不受伤吗?况且你儿子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那时候年轻,我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然惹了麻烦。母亲得了回信,高兴得不得了,每逢家中来客,总是有意翻翻那本散文集,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的我的那张露出两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
那时候前线部队除了战备就是备战,星期天也是随机过——这一周星期二过“周末”,下一周可能就是星期一过“周末”。1984年,我由炮兵排长调任边防某师宣传干事。师政委文子忠刚40岁,精力充沛且思维活跃,每逢周末常带上我跑边防一线。一个师政委,一个干事,一台越野车,一个司机兼警卫员,哪里有哨所有阵地,就在哪里停下来;碰到什么吃什么,聚在一起把政委的一包烟抽完了,“拉家常”式的座谈会也就结束了。这让我很受教育,也积攒了几本子的生动故事。
戍守边防的日子,有苦更有乐,有诗也有远方。
“吃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1985年清明节前夕,《羊城晚报》记者李春晓得知我们部队流传着这首模仿革命烈士夏明翰就义诗改编的战地诗,便与原广州军区宣传处干事麦步初一起,专程来寻找战地诗的作者。战地诗本来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凑成的,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具体作者。但我讲的几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还是感染了李春晓,她让我把故事写下来。
李春晓业务水平很高,只用一个晚上就改出了一篇出色的通讯《追踪一首战地诗》,先是刊登在1985年4月15日的《羊城晚报》一版头条,几天后又被《解放军报》在同样位置转载。这首战地诗由此传遍全国。
凑巧的是,1985年军队高考的作文,竟然是为与《追踪一首战地诗》同类题材的《解放军报》通讯《热血男儿一席谈》配写一篇评论。我自然写得很有心得,也得了一个很高的分数。
离开边防前,已经担任团政治处主任的周杰专门把我叫到老团队为我饯行。临别时,周杰送我一句话:“你是块搞写作的料,这辈子就不要改行了!”
那一天,是1985年8月28日,转眼已经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