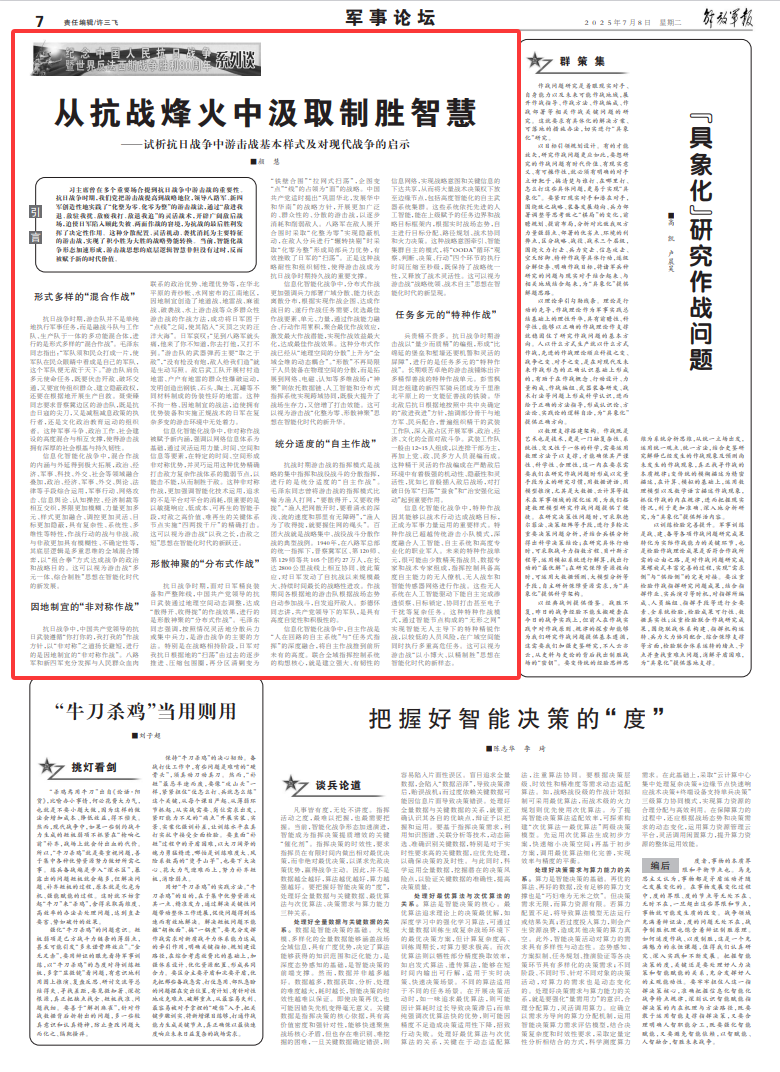从抗战烽火中汲取制胜智慧
——试析抗日战争中游击战基本样式及对现代战争的启示
■颜 慧
引言
习主席曾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创造性地实践了“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法,通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战术,开辟广阔敌后战场,迫使日军陷入顾此失彼、两面作战的窘境,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分散配置、灵活机动、袭扰消耗为主要特征的游击战,实现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势能转换。当前,智能化战争形态加速形成,游击战思想的底层逻辑智慧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形式多样的“混合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并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任务,而是融战斗队与工作队、生产队于一体的多功能混合体,进行的是形式多样的“混合作战”。毛泽东同志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游击队肩负多元使命任务,既要伏击歼敌、破坏交通,又要宣传组织群众、建立隐蔽政权,还要在根据地开展生产自救。聂荣臻同志要求晋察冀边区的游击队,既是抗击日寇的尖刀,又是减租减息政策的执行者,还是文化政治教育运动的组织者。这种军事斗争、政治工作、社会建设的高度混合与相互支撑,使得游击战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与持久韧性。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混合作战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极大拓展,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社会等领域融合叠加,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法律等手段综合运用,军事行动、网络攻击、信息舆论、认知操控、经济制裁等相互交织,界限更加模糊、力量更加多元、样式更加融合、调控更加灵活、目标更加隐蔽,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多维性等特性,作战行动的战与非战、敌与非敌更加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其底层逻辑是多重思维的全域混合博弈,以“组合拳”方式达成战争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这可以视为游击战“多元一体、综合制胜”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发展。
因地制宜的“非对称作战”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遵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方针,以“非对称”之道扬长避短,进行的是因地制宜的“非对称作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充分发挥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政治优势、地理优势等,在华北平原的青纱帐、水网密布的江南地区,因地制宜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众多群众性游击战的作战方法,成功将日军困于“点线”之间,使其陷入“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日军哀叹:“见到八路军就头痛,他来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游击队的武器弹药主要“取之于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就是生动写照。敌后武工队开展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爆破运动,发明创造出钢铁、石头、陶土、瓦罐等不同材料制成的伪装性好的地雷。这种不拘一格、因地制宜的战法,迫使拥有优势装备和实施正规战术的日军在复杂多变的游击环境中无处着力。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非对称作战被赋予新内涵,强调以网络信息体系为基础,通过灵活运用力量、时间、空间和信息等要素,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形成非对称优势,并灵巧运用这种优势精确打击敌方复杂作战体系的脆弱节点,以能击不能,从而制胜于敌。这种非对称作战,更加强调智能化技术运用,追求的不是平台对平台的消耗,很重要的是以敏捷响应、低成本、可再生的智能手段,对敌之高价值、难再生的关键体系节点实施“四两拨千斤”的精确打击。这可以视为游击战“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跃迁。
形散神聚的“分布式作战”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精良装备和严整阵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地理空间动态调整,达成“散得开、收得拢”的作战效果,进行的是形散神聚的“分布式作战”。毛泽东同志强调,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由过去的逐步推进、压缩包围圈,再分区清剿变为“铁壁合围”“拉网式扫荡”,企图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战略。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开展更加广泛的、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以逐步消耗和削弱敌人。八路军在敌人展开合围时采取“化整为零”实现隐蔽机动,在敌人分兵进行“辗转抉剔”时采取“化零为整”形成局部兵力优势,有效挫败了日军的“扫荡”。正是这种战略耐性和组织韧性,使得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的重要支撑。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分布式作战更加强调兵力部署广域分散、能力状态离散分布,根据实现作战企图、达成作战目的、遂行作战任务需要,优选最佳作战要素、单元、力量,通过作战能力融合、行动作用累积,聚合最优作战效应,激发最大作战潜能,实现作战效益最大化,达成最佳作战效果。这种分布式作战已经从“地理空间的分散”上升为“全域全维的动态耦合”。“形散”不再局限于人员装备在物理空间的分散,而是拓展到网络、电磁、认知等多维战场;“神聚”则依托数据链、人工智能和分布式指挥系统实现跨域协同,既极大提升了战场生存力,又倍增了打击效能。这可以视为游击战“化整为零、形散神聚”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升华。
统分适度的“自主作战”
抗战时期游击战的指挥模式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进行的是统分适度的“自主作战”。毛泽东同志曾将游击战的指挥模式比喻为渔人打网,“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百团大战就是战略集中、战役战斗分散作战的典型战例。1940年,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等共105个团约27万人,在长达2800公里战线上相互协同、彼此策应,对日军发动了自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作战期间各根据地的游击队根据战场态势自动参加战斗,自发追歼敌人。彭德怀同志讲,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具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自主作战是“人在回路的自主系统”与“任务式指挥”的深度融合,将自主作战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的构想核心,就是建立强大、有韧性的信息网络,实现战略意图和关键信息的下达共享,从而将大量战术决策权下放至边缘节点,包括高度智能化的自主武器系统集群。这些系统依托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在上级赋予的任务边界和战略目标框架内,根据实时战场态势,自主进行目标分配、路径规划、战术协同和火力决策。这种战略意图牵引、智能集群自主的模式,将“OODA”循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四个环节的执行时间压缩至秒级,既保持了战略统一性,又释放了战术灵活性。这可以视为游击战“战略统领、战术自主”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呈现。
任务多元的“特种作战”
兵贵精不贵多。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以“量少而质精”的编组,形成“比绵延的堡垒和堑壕还要机警和灵活的屏障”,进行的是任务多元的“特种作战”。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战锤炼出许多精悍善战的特种作战单元。彭雪枫同志组建的新四军骑兵团成为千里淮北平原上的一支能征善战的铁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敌进我进”方针,抽调部分骨干与地方军、民兵配合,普遍组织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武装工作队一般由12~15人组成,以连排干部为主,再加上党、政、民多方人员混编而成。这种精干灵活的作战编成在严酷敌后环境中有着极强的机动性、隐蔽性和灵活性,犹如匕首般插入敌后战场,对打破日伪军“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起到重要作用。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特种作战因其能够以战术行动达成战略目标,正成为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样式。特种作战已超越传统游击小队模式,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军人。未来的特种作战单元,很可能由少数精英指战员、数据专家和战术专家组成,指挥控制具备高度自主能力的无人僚机、无人战车和智能传感器网络进行作战。这些无人系统在人工智能驱动下能自主完成渗透侦察、目标锁定、协同打击甚至电子干扰等复杂任务。这种特种作战模式,通过智能节点构成的“无形之网”实现智能无人主导下的特种精锐作战,以较低的人员风险,在广域空间能同时执行多重高危任务。这可以视为游击战“以小博大、以精制胜”思想在智能化时代的新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