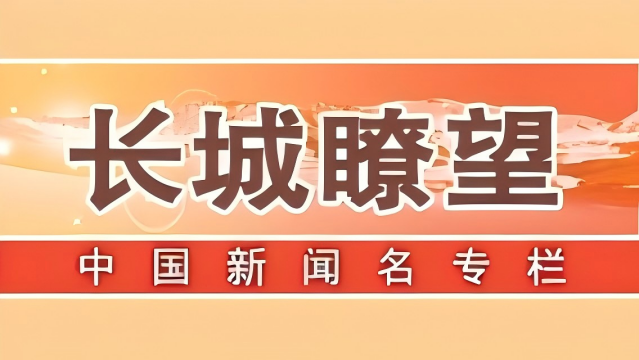第一粒扣子
■张明刚
虽然还未戴上领章、帽徽,但是,我已真切地穿上那身向往已久的军装。是的,我即将离开可爱的家乡,奔赴远方火热的军营……43年过去了,兵之初的那些事,在我的记忆里,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愈加鲜艳。
一
那时候,18岁的我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感觉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美好。
那是一个深秋的清晨,我走进厨房,坐在灶台边陪着母亲煮红薯稀饭——这将是我当兵之前在家中的最后一顿早餐。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着柴火,一边轻轻地叮嘱我:“明刚,你今天就要参军走了。到了部队,别惦记妈妈,不要想家,要听首长的话,好好干!”
我连连点头,“嗯嗯”不止,却不敢直视母亲——怕她看见我眼里的泪水,更怕自己忍不住哭出声来。可转过身去,我对着镜子里那个穿着崭新军装的自己,嘴角又忍不住往上翘……一门心思想当兵的我,真到了要走的时刻,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秋阳杲杲,万物苏醒。早饭后,家里就开始陆续来人。叔伯婶娘们在欢声笑语中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夸我“出息了”;老表伙伴们羡慕地围在我的身边,将我的军装摸了又摸、看了又看;几个小朋友兴高采烈地跑进来,笑容灿烂地叫我“解放军叔叔”;平时不爱说话的邻家大爷,也拉着我的手,和我说了不少知心话,临了还塞给我两个煮鸡蛋,让我“路上填填肚子”。
我把鸡蛋揣进裤兜里,一边一个,双手插兜,紧紧握着——我突然明白,这哪里是两个普通的煮鸡蛋,分明是父老乡亲的祝福和期盼。
那时的村子还叫生产大队,镇子叫人民公社。那一年,我们全大队共有3个青年参军,一个是我,另外两个是我的同学……我们出村的第一站是到公社集合。大队唯一的一台拖拉机停在村子中间,柴油发动机已在“突突”声中冒着黑烟,两位同学也已站在车厢里向大家挥手致意,他们胸前的光荣花和绶带分外耀眼……
我告别敲锣打鼓、夹道欢送的乡亲们,随即登上了拖拉机,与两位同学会合。这时,二弟从欢送的人群中快步跑来,扔给我一大挎包书,气喘吁吁地说:“哥呀,你怎么忘带你的宝贝书了呢?”是呀,那时的我边耕边读边写作,是个文学青年,正做着将来当作家的美梦,而书是我的心肝,是必须带走的。
到公社集合后,我才知道,当年全公社36个征兵名额,我是最后一个被定下来的。我父亲去世早,家里缺乏男劳力,我又是长子,刚开始,大队和公社领导担心我家里没人种地,不太同意我走。因为母亲的一再坚持,我最终获准入伍。
她挨个去找大队和公社领导,见人就央求表态:“既然我儿明刚体检、政审都合格,你们就让他当兵去吧,天大的困难我们自己克服,绝不给政府添麻烦!再说,明刚已经种了两年多地了,他二弟也长大了……”
得知母亲为我奔走的事情后,我泪水模糊了双眼。在我们乘坐的车即将离开公社、前往县城时,我突然转过身去,朝着家乡的方向,默默地在心里说:“娘啊,您放心,儿子一定要当个好兵,绝不辜负您的一片苦心!”
二
我的心早飞过山岗,飞过平原,飞过城市,飞向数千里之外的军营,渴望开始新的军旅生活。然而,当时的交通条件,使我不得不度过好一段“慢时光”。
我们在县城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正式出发。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点,早点到军营,早点摸到枪,早点成为一个真正的兵。
可是,无论是乘坐的闷罐车,还是换乘的绿皮火车,跑起来都是一样慢,在“哐当哐当”响的节奏中,可以数清窗外的树。从湖北随州到黑龙江绥芬河,我们走了四天多时间。
记得是1982年11月3日的凌晨,我们到达北京站。下车后,长长的新兵队伍被带到站前广场,然后排列整齐,坐在各自的背包上。寒风像小刀子似的直往衣领里面钻。大家穿着棉衣大头鞋,还是冻得直跺脚。
接兵的王连长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给年纪最小的一个新兵穿上。然后,他站起来大声说:“同志们,北方天气寒冷,可能会越来越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可以适当活动活动,进行抗冻训练。”
听了王连长这话,我意识到,接兵干部对我们一直保密的目的地,肯定不是北京,应该是东北更冷的地方。东北到底有多冷?那边的军营该是个什么样子?我满心期待着。
天亮后,我们果然转车继续北上。从北京到沈阳,从沈阳到长春,从长春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牡丹江。
一路上,我们既好奇又紧张,互相凑在一起嘀咕:“到底要去哪里啊”“肯定是个重要的地方”……现在想明白了,那时我们一步步靠近边防,每多走一站,就离边防战士的身份更近一分。
长路漫漫,时光难熬,我那一挎包书便成了香饽饽,不少战友向我借书看。我总说:“借是可以的,但要记得必须还我!”
到达牡丹江的时候,天已黑透了。我们被接到军供站,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晚餐。这对连续吃了几天干粮、吃得有些倒牙的我们来说,印象非常深刻。饭后,入住火车站旁的旅社。一路奔波、十分疲劳的我们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上了火车。这次每到一个相对较大的站,都要分流一批新兵。最后到达终点站的只有几十个新兵了。下了火车,又换乘汽车。汽车在山沟里绕了半天,最后停在一片空地前。这里有几辆马车、牛车和几位官兵——他们应该是来接新兵的。
我和其他几个新兵一起坐上一辆铺着干草的牛车。“出发!”接兵干部手一挥,驾驭牛车的老兵便“嗒嗒嗒”地赶着牛往前走。
放眼一望,千里冰封,一派北国风光。车轮压过白雪皑皑的崎岖坎坷的土石路,发出“吱吱”的声响,颠得人屁股生疼。看着越来越荒凉的大山,我心里却突然踏实了——这就是要去的边防连队。我的兵之初,就要从这里正式开始了。
三
边防连队地处素有“五月雪九月霜”之称的偏僻之地,远离村镇,环境条件异常艰苦,文化生活也很枯燥。大家却以苦为乐、不畏艰难,你追我赶、不甘落后,个个都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我的新兵生活,从进驻新兵排开始。进屋后,我们在班长的指导下,进行直线加方块式的整顿。班里12个人,班长打头,副班长断后,在大通炕上一字排开各自的被褥,然后叠成整齐的豆腐块。洗脸盆、毛巾、牙具等物品摆放,也都是笔直的一条线。
炕要自己烧,燃料是就地取材,到山上把枯倒的木头拉下来,然后锯成段、劈成块,俗称“拉劈烧”。菜是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主食是杂粮,玉米碴子、高粱米、二米饭,偶尔吃顿大米或白面馒头,就算改善伙食了……班长问苦不苦,所有人都说不苦。
一天后,新兵到齐,我们开始了正规的新兵训练。出操、队列、体能、投弹、射击……一直练到天黑,有时夜晚还自觉加训。5公里越野,跑不动了,战友帮你拉着,没人落下;战术训练时,在地上爬,衣服磨破了,膝盖磨出血,也没人喊疼;一天的正步踢下来,晚上连炕都爬不上去……班长问累不累,没有一个人说累。
最难忘的是紧急集合。训练进行到一周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我们睡得正香,“嘟嘟嘟——”哨声突然响了。大家一下子从炕上弹起来,摸黑找衣服、打背包。有人穿错裤子、有人鞋子穿反了……还有人背包打得散架,跑出去的时候,背包掉在地上,只能抱着跑。
班长站在大门前,看着我们说:“下次再这么慢,就围着操场跑10圈。”后来,夜里紧急集合成为常态,有时一晚要拉动几次。练得多了,我们闭着眼睛都能穿衣服、打背包,哨声一响,3分钟就能集合完毕。现在想起来,那些紧张的夜晚,不是“折腾”,而是在练我们的“快”和“稳”——边防线上随时可能出情况,容不得半点闪失。
新兵们尽力施展各自的本领,争抢着为连队作贡献。有的战友训练好,班长总夸他“是个搞军事的料”;有的战友学习好,政治课上总能回答出问题……我呢,业余时间看书读报、写写画画,没什么突出的,就想着早点起床,打扫卫生。可是,一连三天,我都没捞着机会,因为扫把在前一天晚上,已被别的新兵藏了起来。
“那我还能干点什么呢?”对自己的文字基础颇有信心的我,苦思冥想之后,自告奋勇担任连队宣传员,办黑板报,为战友们加油鼓劲。一开始,我办得不怎么好,可我每天都坚持练习。慢慢地,我办的黑板报成了连队的“风景线”,战友们时常来看。
苦和累的连队生活充满了温馨。谁的父母或者对象来了,连长、指导员都会亲自看望,炊事班也会设法加两个菜;谁感冒生病了,班长会送来里边卧着两个鸡蛋的病号饭;谁家里出了大的变故、遇到困难,每月拿着10元津贴费的战友会3块5块的凑钱……我把这些事情写在黑板报上,并择优投给报社。
1个月后,团宣传股股长手里拿着1份《前进报》来到连队,点名要见我。原来,在这张最新出版的报纸上,登着我的一篇豆腐块文章,文末署名写着我的单位和姓名。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后来,《解放军报》也刊发了我的一篇稿子,团政治处主任还来连队见了我。
3个月后,新兵训练结束。上级考核全排30多名新兵,成绩大多是良好和优秀,无一人不及格。
于是,新兵们都戴上了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指导员在讲话中说,这标志着我们完成了从一个社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也意味着我们顺利度过了兵之初。
四
老话说:时,一年四季在于春;人,三岁可以看到老……而我要说:兵,初期关系着未来。
那时候的我们,真实、纯粹,没有杂念,全凭本心。训练好的战友,肯吃苦、讲方法,后来当了军事干部;学习好的战友,爱琢磨、肯钻研,后来成为各种人才……这使我感到,新兵怎样对待训练,怎样对待学习,怎样对待生活,其实就是在告诉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兵。
多年以后,每每想起新兵生活,我心里总会生出一种别样的情感。新训苦是真的苦,累是真的累,可正是那段经历,教会了我最朴素的道理:兵之初就是军旅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只有扣好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正、走得远。
回头看,新兵连的苦和累,就像个筛子,它筛掉的是娇气、懒气,留下的是骨气、志气。我们上山拉柴,两个人扛一根木头,汗水湿透了军装,但没人放下;晚上紧急集合,再累也不会偷懒。苦,从来不是白吃的,它让我们学会坚持,学会担当,学会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这些,恰恰是一个新兵最需要的素质。
现在,军营里有智能手机、电脑,有现代化的训练装备。条件好了,兵之初的那份心不能丢。比如,对军装的敬畏心,对训练的吃苦心,对平凡事的用心等。时代变了,兵的本色不能变,比如,不怕苦、不怕累、不服输,坚持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每一个课目都练精等。
多年来,我总是不时想起当兵之初的那顿稀饭、那俩鸡蛋,想起那时的杂粮、那时的热炕……以及那时深夜紧急集合的哨声。这些印记,成为我后来人生的指南——无论路走多远,都不忘自己当初是怎么穿上军装、怎么扛过那些苦日子、怎么凭着一股冲劲往前走的。
兵之初这段刻进骨子里的印记,是一份藏在心里的财富。它教会我:当兵,要像边防的树,扎根土地,不怕风吹雨打;做人,要像军营的歌,朴实有力,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