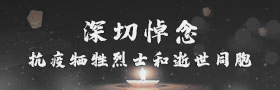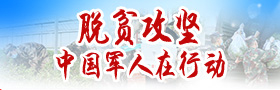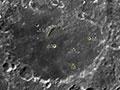初夏的气息,馥郁芬芳。夕阳下,朱京慈教授静静地站在操场边,看着一队队跑着圈的护理专业女孩。她们流着汗,欢笑着。晚霞被夕阳温柔的光线轻轻拉扯,大块的碎片紧贴女孩们绯红的脸颊,煞是好看。那一刻,朱京慈似乎被什么吸引住,陷入沉思。
我猜,此刻她定然在想:“我也这样年轻过。”
我的母亲与朱京慈同岁,出生在1956年。我不清楚那个年代出生的女性究竟带着怎样的“烙印”,只能感受,只能听说。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便当知青,后来到国企工作,结婚,相夫教子。飘着清香的被褥和桌上家常味的饭菜,是我想起60岁的母亲,最为温馨的印象。她的同龄人是怎样的生活状态?我常常好奇着。
不同的生活背景,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并由此衍生出关于“幸福”二字不同的定义。对于母亲,15岁,长在一个大家庭,与一大群天真烂漫的姑娘到离家不远的地方插队,与姐妹们一起憧憬人生,憧憬美满的姻缘,并一步步去实现,这就是幸福;对于朱京慈,15岁,听着军号声长大的女孩,瞒着父母报名参军,最终在白玉兰盛开的时节走进第三军医大学,循着朦胧却坚定的初心,一直行走,这就是幸福。

朱京慈的记忆里,那些在春天里生长出硕大花朵的玉兰树,曾经沿着俄式风格的基础部大楼一直通向校园里一个幽静的所在——护士学校的白色小楼。1973年,17岁的朱京慈和她的同学们,在这座小楼里,第一次听说了“南丁格尔”这个美丽的名字。特殊的年代,连看本外国名著都得悄悄的。今天,这座小楼已经是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所在,傍晚总有红火的坝坝舞;而南丁格尔的瓷像也静静地立在年近60岁的朱教授的办公桌上。
“两年时间,在小楼里上课,也住在小楼里。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头要住30号人。”朱京慈告诉我。其实人多也好,不怵,比如姑娘们把一具好不容易才借出的人体骨架标本直接拿回宿舍,挂在上下铺柱子上,熟悉解剖结构。
胆子就这么给练大了。大坪医院实习结束,外科主任王海棠点名要了朱京慈:“这丫头不错,胆儿大。”因为王海棠发现,科里有个高个子的实习护士会利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连续几小时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医生做手术。“我了解手术过程,对护理也有帮助呀。”朱京慈说。
20岁出头的外科护士朱京慈除了护理,还额外学习了针灸,给病人扎还真有效果,后面居然有人主动上门请她“施针”。当然,“小护士为病人针灸”在今天的“医患关系”背景下颇为冒险,可当年一个场景却能证明此举的稀松平常:饭点,给病人的送饭车来了,外科主任、医生、护士,不管身份,都纷纷上去,热情满满地给卧床的病人打饭、喂饭。
和谐的环境造就了热爱护理事业、却疏于名利的朱京慈,她说:“我喜欢被人领导着,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想要被人“领导”,却意外地成为“领导者”,是朱京慈军旅人生的际遇。出色的外科护士被提拔为新组建的神经外科护士长,神经外科护士长被提拔为医院护理部主任,医院护理部主任被提拔为学校护理系主任,一路走来,全是故事。当年,一位老首长曾对朱京慈说:“你呀,工作挺努力,就是不爱到机关走动,这有点吃亏哦。”那时连行政级别都搞不清楚的朱京慈心里直嘀咕:“怎么走动呀,机关也在上班呀,我去打搅别人合适吗?”
一个岗位一个平台,对于想做事的人来说,平台就是一对翅膀。朱京慈不想当“官”,一心要把事做“漂亮”,平台给了她更多施展抱负的机会。
当护士长,适逢医院提倡取消“陪护”,她带着从农村招来的护工一点一点地做病房清洁,一手一脚地教她们为患者做生活护理;每天晨间换床单时也一定出现在病人的床头,悉心了解每一个病人的情况。当护理部主任,她仍习惯于忙碌在临床一线和抢救现场,大抓护理质量和护士培训,医院全国注册护士考试通过率总在90%以上;当护理系主任,她主动思考“我们的医学进展迅速,我们的护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护理学科该怎样建设?”,诚恳的态度得到程天民、杨宗城等大家“指路”。
简简单单的朱京慈是幸运的,站在护理系承前启后的平台,她参与和目睹,一所军医大学建立了学历教育与任职教育并重的完整护理教育体系,构建了拔尖创新护理人才与新型实用护理人才相结合的护理人才培养模式。让本科学生走出国门看世界,亦是学校的“第一次”。每届班子都在自己任期内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由基础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内科护理学、野战护理学、急救护理学、社区护理学、老年护理学、护理研究、护理心理学等25门课程组成的专业课程体系。护理系培养的学生中有2人先后荣获41届和42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1人荣立一等功,2人获得重庆市争光贡献奖,2名研究生获重庆市优秀学位论文,本科生参加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始终保持100%的通过率。甚至,她与两任搭班子的政委也是“相处甚欢”。“李文荣政委转业命令已到仍主动为我分担学院的工作;我的想法与寇晋政委一交流,他就能用心琢磨并把这些想法外化出来。”


幸运的背后自然是超常付出。这些付出的时间,大大早于收获“幸运”的时间。1987年,在八岁的我拉着妈妈非要买一块蝴蝶酥的时候,还有两个月就要当妈妈的朱京慈却执意踏上了去南京求学的火车,因为那里有美国来的老师,有最前沿的护理知识和技术。不能想象,当年,南京的老师同学看见这样一个拖着大箱子、挺着大肚子的女学员,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临产前4天,她才坐着飞机回到重庆。
2009年,从领导岗位退下、做教授的朱京慈一心扎进了“创伤危重症肠内营养支持”的研究,有专家劝说“想从护理角度取得进展很难”,她却安静得似乎“消失”了,直到拿下国家自然基金课题、论文被选入F1000,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护理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奖项陆续“爆出”,大家才明白,“朱教授”不是“消失”了,而是“闭关”了。
记得,我在操场遇见她时,与她有这样一段对话。
“不要写我,我只是护理系一名普通的教授,实在没有什么突出业绩。”她说。
“我要写的不仅仅是你,是想透过你,去了解我们几代军医大学护理人身上的一些共性和特质。”我说。
她笑了,然后讲起了她的故事。故事的起点是盛开的白玉兰。我分明看见,夏天已经来临,虽然没有花朵,那一棵棵玉兰树却分外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