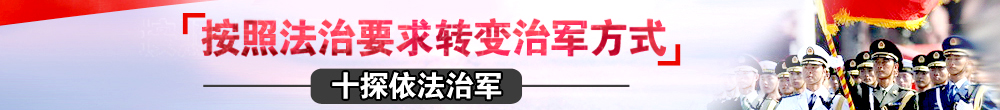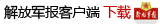“天皇制”得以保留的原因
战后象征天皇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统治机构的连续性,思想、心理、传统权威意识的连续性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天皇和皇室自身努力树立“大众天皇制”的形象,统治集团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出发不断加强和恢复天皇的地位与权威,国民中间仍潜藏着对天皇制的传统感情。
二战后,盟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10月4日发布自由指令,拉开了从思想意识领域清除天皇神化意识的序幕,强调了取消对政治、宗教自由的限制。
鉴于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国民的意志,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向国民发布《人间宣言》,否定了“天皇为现世神”,确定了自己“人”的地位。表面看这是否定了天皇的神性,但实际上该诏书却非常巧妙地维持了天皇的神性,维护了天皇是“神裔”的观念。
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公布,给日本投降后展开的有关天皇和天皇制的争论,基本上打上了“终止符”。同时,新宪法的有关规定是基于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既要铲除旧有天皇制,又要保留天皇的原则制定的。这种制宪指导思想上的矛盾,必然会在宪法中,以及宪法与现实的矛盾中反映出来,导致战后日本政治领域中出现了有关天皇问题的种种奇怪现象。
战后以来,为加强天皇的地位和权威,日本上层统治集团恢复旧天皇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组阁后,明目张胆地要复活某些旧的传统制度;1950年,美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美国和盟军总司令部放弃日本非武装化政策,要求日本重新武装;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了主权。盟军总司令部撤消,但美军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继续驻扎日本。
据渡边治所著《日本国宪法修改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介绍,为实现天皇元首化必须修改宪法,为防止民众反对,吉田内阁、鸠山一郎内阁、岸信介内阁相继以“自主宪法”为名,渐进式修改宪法,意欲将“象征”天皇变为元首,将 “放弃战争”变为“自主防卫”。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复辟旧天皇制的具体行动之一,同时,另一项复辟的小伎俩也着手实施——实行“年号法制化”运动。自明治以后日本的年号实行“一世一元制”(一代天皇一个年号)。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裕仁天皇年号仍延用“昭和”。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裕仁年老,然而新的《皇室典范》等并无年号的规定,政界上层和神道系统的人物十分担优,积极主张应使年号法制化。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79年6月由国会通过了年号法案,成为抬高天皇权威的一次大飞跃。
“天皇制”之所以得以保留,除了国内对天皇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国在其中也起了不小作用。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多次批准宣战的日本帝国统治者裕仁天皇始终没有现身。而美国作为处理战后对日问题的主导国家,却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原因何在?
美国人当时发现,日本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天皇制,及特殊的政治角色——天皇,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保存天皇制为“诱饵”,促使日本投降,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美军伤亡,而日本也迫于形势压力和迎合美国人的心态,由天皇来宣布投降,这就为战后保留天皇制成为可能埋下了伏笔。
日本投降后,美国又依托天皇的精神权威,达到保持日本社会秩序稳定,进而顺利实现对日占领的目的。于是将天皇塑造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引领者”的形象,为其在日本传播美式民主主义理念、有效地占领和管理日本铺平道路。同时又将天皇的地位界定为“象征性”存在,仅仅具有从事国事行为的权利,剥夺了天皇在明治宪法下的一系列军政大权,由此舒缓来自美国国内及盟国方面要求废除天皇制的舆论压力。美国又将代表君权主义的天皇制与民主主义嫁接起来,旨在将天皇塑造为推动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的核心人物,减缓来自保守层要求提高天皇在宪法中地位的阻力。
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乔治·凯南也说:“面对一个真正友好的日本和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我们美国人会感到相当的安全,但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国和一个真正敌对的日本对我们的威胁,已经为太平洋战争所证实,一个敌对的中国比一个敌对的日本更糟,然而,共产主义在大部分中国的胜利,必然增强日本共产主义的压力……获得成功,那我们面临的日本将显然是一个敌对的日本。”美国人的意图之一,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将日本改造为友好的“民主国家”、打造成窥视、牵制中国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