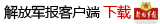国家战略能力主要指一个国家着眼本国安全利益目标,为预防和应对可能的危机、冲突或战争,所能调动和使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这是一个涉及多因素的复杂动态体系,既包括国家的土地、矿产、人口等资源要素,也包括国家经济机制、政治机制、军事机制等机制要素,还包括经济能力、科技能力、军事能力等能力要素,以及国民素质及精神状态、领袖集团素养、战略筹划与决策能力等精神要素,而决不是单一力量的反映。
增强国家战略能力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统筹考虑,但毫无疑问,军事力量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支撑力量,其中最基础、最根本、最核心的,就是军队作战能力。这是硬实力中的硬实力。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综合国力的发展。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七大要素。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国家战略能力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国家战略能力是沟通和连接现有综合国力与未来综合国力的桥梁,即现有综合国力→国家战略能力→未来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形成的基础,而国家战略能力对综合国力也有反作用,国家战略能力对综合国力发挥着强大的制约作用,影响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发展。
从宏观角度看,综合国力强调静态分析,但国际政治千变万化,国家战略能力就是适应这种变化的一种动态平衡。任何一个国家要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夺取国际政治斗争的战略主动权,就必须提高国家战略能力。正如若米尼指出的:“富有黄金的大国,其国防可能有时很差。历史证明,最富的民族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和最幸福的。从军事力量的天平上来看,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但我们仍需毫不迟疑地承认,要使一个国家具有最强大的国力,并能经受长期战争,就必须要有英明的军事制度、爱国精神、大量财富和社会信用,而且要能把这些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
基辛格也持同样观点:“今天实力的含义较以前复杂了。具有军事力量并不能保证就具有政治影响。经济巨人在军事上可能是软弱的,而军事实力也许并不能掩盖经济上的虚弱。”因此,“只谈一种力量对比是错误的,因为有若干种力量对比,而它们必须是相互关联的”。 尽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但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国家间以综合国力竞争为主线的经济发展模式。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和条件往往突出表现在国际竞争力上。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下,与世界整体中各国的竞争比较所能创造的增加值和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的系统能力水平,主要包括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影响、金融实力、基础建设、企业管理能力、科技实力和人力资源等八大因素。国际竞争力就是以国际政治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为目标、以科技创新和率先突破为制高点、以军事力量为威慑手段和以文化、人才及人的素质的竞争来进行综合国力的角逐。因此,发展,充满竞争;竞争,推动着发展。
2010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称,中国大陆已由第20位上升至第18位,居于“金砖四国”榜首;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分析了1990~2008年中国在全球100个主要国家的位置及其变化,中国国家竞争力由第73名上升至第17名。中国经济的增长、军力的加强、核威慑的存在,不仅提升了我们未来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的能力,而且也使国家利益拓展在国际竞争力增强的同时,得到有效护卫。
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塑造,而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需要以我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能力提升为前提,只有这二者增强,战略目标才能由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转向维护国家利益拓展提供有力战略支撑。因此,国家战略能力强弱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未来综合国力的强弱,乃至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起落。这一点可以从核武器的发展史中管窥一斑。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美苏的同盟关系走到尽头。在以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摩擦、严重的危机,甚至是剑拔弩张的冲突,但美苏之间的冷战没有变成热战,小约瑟夫•奈认为,其主要原因既不是发达国家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想打仗,也不是超级大国追求有限的扩张主义目标,更不是新现实主义领军人物肯尼思•N•华尔兹认为的那样,因为两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两极结构的稳定性,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核武器和核威慑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美苏之间核军备竞赛的结果是形成核均势,核均势不同于传统均势,尽管核均势的结构内部不乏变化和震荡,但它的走向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使平衡精确化和稳定化了 。核均势使“恐怖的和平”得以维持,这是因为“传统均势遭到破坏,一般只对欧洲的部分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而核均势一旦被破坏,美苏自身安全就会受到致命威胁”。 所以,美苏核均势的威慑力,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冷战的“热化”。由此可见,核威慑力既是国家展示国际地位强弱的一个战略指标,也是一个国家战略能力高低的具体体现。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戴维•兰普顿在其《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将要获得并维持有效的威慑。中国正处在核威慑能力变化的关键时刻,即将拥有灵活可移动的陆基洲际核导弹系统和更实用的海基洲际核导弹能力。部分推动这一能力提升的,正是美国常规武器数量和精准度的提升,中国人担心这些常规武器被用来攻击中国核能力,而无需破坏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禁忌。
美国安全体系中的一些人到现在也没有公开接受当年苏联体制中的一些明显事实:苏联不遗余力地实现了二次核打击能力,苏联目标是在最低可能水平上维持危机时刻稳定的相互核威慑能力。中国需要获得最低意义上的核威慑能力,美国也需要对自身战略弱点有个痛苦的认识和接受”, 他指出,在冷战时期,核战略家大多数时候都相信,如果超级大国开发对有效二次核打击产生威胁的进攻或防卫系统,将会对整个体系带来不稳定,但今天,有些美国战略家却不接受中国获得安全威慑的权利、能力以及决心。中国能够也将以能够承受的代价做到。戴维•兰普顿认识到,美中应当开始关于如何在最低程度上实现稳定威慑的谈判。
今天,核武器作为国家的绝对实力已接近了巅峰,以至于相对实力的变动再也无法撬动这种毁灭性的力量平衡,加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能力的跃升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增强的现实,特别是在地区和世界上地位日益重要,令西方传统大国越来越难以一超独霸而产生畏惧。西方的世界末日预言家马丁•雅克在其《当中国统治世界》 一书中甚至声称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将会让美国相形见绌,他预言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影响力将会在2025年之前赶上美国,并且在2050年之前远远超过美国。
英国学者珍妮•克莱格在其《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一书中指出,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中国正日益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参与者,新世界的轮廓正在形成。新保守派构想了以美国作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现在这种构想已经开始黯然失色,中国采取多边战略,运用和平发展的构想来促进一个多极世界的形成,中国的崛起标志着各国将在一种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中,以比较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际事务。这正如参与华盛顿对华政策讨论者埃里克•安德森在《中国预言:2020年及以后的中央王国》 一书中论证的那样,事实上北京的最高目标是营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以合法的政治权力而不是高压手段为基础来发展经济并获得地区主导地位。2020年的中国既不会推行霸权主义,也不会是排外主义的。2020年的中国仍将会专注于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成为国际社会中备受尊敬的成员。
上个世纪90年代伊始,人们已经见证了传统大国衰落和新兴强国崛起的盛大演绎。新技术继续为军事变革创造条件,不论其会在军事方面带来何种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各国仍需要对自己的安全防御负责的话,那么,实力所带来的安全困境无疑都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实力安全困境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一个异常持久的特征。
在《变化的战争:走入第四代战争》一书中,作者总结道:第一代战争体现了横队和纵队战术,就是在主要作战点集中兵力,它部分以技术为基础,部分以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的社会变迁为基础;第二代战争因武器在质和量上的变化而产生,依靠的是集中火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和法军信奉的“炮兵征服、步兵占领”信条,使这一代战争达到巅峰;第三代战争是机动战,1939年的德国军队在战场上运用了新的作战能力,即坦克、机动火炮、机械化步兵、有效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无线电通信等技术,使机动和进攻的作用再次显现;第四代战争与时间有关,是以10年而不是以月或年作为计算单位,即中国共产党人战斗27年,越南人战斗了3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战斗了18年,巴勒斯坦人从1967年一直战斗至今,阿富汗人用10年时间打败了苏联,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打的也是这种战争。任何想要改变政治力量对比的人,只有非常规战争才能有效对付占据优势的力量,这种战争成功对抗了超级大国,这是未来战争的特征。第四代战争不仅靠军事实力,因为持久战需要以国家战略能力作支撑。
战争形态发生演变,战略对抗就在实力带来的安全困境中寻找解决的路径。有一位澳大利亚商界领袖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全都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逃离其外。我不希望美国忘记他们的价值观。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住在中东,而阿拉伯人有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念,正像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一样。中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对于美国政策和美国社会而言,这是个大问题。你得拥有无限的耐心。在竞争方面,我崇拜美国人。你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是第一。但那会持续多久?印度将会强大,但永远不会是个阻碍。中国会与美国竞争世界领导权吗?就我所能想象的,它永远不会争夺全球领导权,因为美国人的能力独一无二。你们富有创新精神,拥有快速决策的能力。你们拥有政治能量,你们还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平台。你们有创新和快速决策,但中国没有。如果你们集中于自身力量,中国人就能够更关注他们的优势力量,比如纪律、团队精神、人力资源以及坚忍不拔等。创新天生就属于美国。” 这正如部分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挑战主要并不在军事上,美国应当努力培养一种环境,使得中国的重点诉求能够被引入其中,而不会游离于其外而以军事方式表达出来。
如果美国一味将中国当作一个以军事为重点的国家来看待,那么,反而会推动中国向着这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前进。比如,2007年初,中国摧毁了一枚退役轨道卫星,部分就是出于展示不向美国的太空威胁屈服的姿态的目的。但是,大国之间力量增长与国家利益的零和关系所引发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及中国经济力不断增长导致的溢出效应具有引发冲突的可能,因此,美国应当提升与中国周边大国以及其他大国的关系,不仅因为这些国家可以成为抗衡中国的堡垒,而且这具有由相互依赖的关系而部分化解安全困境的内在价值。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中国威胁论”的视角,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在西方心目中战略对手的形象早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
美国学者妮娜•哈奇格恩和莫娜•萨特芬在她们撰写的《美国的下个世纪——美国如何在其他大国崛起的时代里保持繁荣》一书中认为,“9•11”恐怖袭击,世界格局大变,但之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却让起初人们对美国的同情迅速烟消云散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处理中东以及恐怖主义之外的问题,而此时美国人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印度经济的腾飞,报纸头条充斥着钢铁短缺、美国贸易赤字、人才流失海外和移民的新闻。中印两国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日本的军事复苏和欧洲实力的扩张,对于美国的生活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中国问题上,我们似乎又走上了那条大国对抗的老路。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冷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挑战已不再那么绝对,甚至更加多样化。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是阻止朝鲜核武器力量的一个关键力量,在此情况下,人们怎么能够得出结论,认为今天的中国将会成为另一个苏联、成为美国的敌人呢?面对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和中国乃至俄罗斯和印度的利益是趋于一致而非相左的,因此,我们并不清楚美国对于大国应采取何种战略,但我们最好学会如何与中国人相处。
英国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说:“历史学家能为当代世界贡献什么呢?他们的主要功能,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记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其所著《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一书中写道:“美国总是赢得战争,却输掉和平。但这两个部分其实都不正确。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美国被迫与对手达成维持僵局的协议,10年之后在越南,美国显然是输掉了战争。美国自认为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充斥着冲突和暴力,美国曾经为了各种目的而走向战争——1775年是为了独立,1812年是为了荣誉和贸易,1846年是为了领土,1861年是为了国家统一,1898年是为了人道和帝国,1917年是为了中立的权利,1941年是为了国家安全。自1945年以来,这个国家在亚洲投入了两场结局可悲的有限战争,在中东发动了一场短暂的冲突,一举击败萨达姆•侯赛因,又在伊拉克卷入旷日持久的斗争……”,他反思的是:美国是一个经常就别人生死存亡单方面做出决定的世界大国,这种关乎众多人生死的决定,有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因此,美国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和诚实的态度来行使美国权力,如果不能,那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直接的、而且经常是悲剧的影响。
作者通过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政策和决策者的思维程式,以及他们所要面对的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因素的分析,认为“9•11”之后,这些都并没有改变,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悲剧还会不断重演,美国的全球战略将使战争常态化。我们不能改变别人的思维方式,但我们需要准备应对可能的威胁,只有备战、能战、敢战,才能化解危局,走出战争的阴霾。这就是一个国家战略能力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因为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没有能力,就没有话语权;只有实力和能力,才能换来和平与尊严,这是历史上亘古颠扑不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