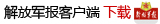从史学价值的角度,如何考证这本历史书籍呢?愚以为至少有几下几点:
其一,属南京大屠杀最早的第一手过硬史料。蒋公榖先生以亲眼目睹的南京大屠杀史实,逐日记载自己身陷南京难民区三个月的切身经历,其资料属于第一手的过硬资料。特别是能够在1938年8月印刷并流传于社会,属最早的直接披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客观证词。由于是直接当事人亲手记述,并在记忆清晰的情况下写成的,应是真实、鲜活、客观、可信的。
其二,内容涵盖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暴行。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主要表现在烧杀淫掠四个方面。对于这些,《陷京三月记》都有清楚细致的概述,为后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提供了依据。此外,还对美侨李格斯等南京安全国际委员会成员救助难民,红十字会在金陵大学农场掩埋12万具遇难同胞尸体等作了记录,其内容广泛,生动具体,深刻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种种暴行。
其三,与其他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形成了证据链。近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在海内外陆续被发现,如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证人拉贝、马吉、魏特琳、威尔逊等日记;以及加害者日军官兵东史郎、中岛今朝吾、上羽武一郎等人的日记,还有一大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资料,都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珍贵证词。蒋公榖及其《陷京三月记》从一个特殊的视角,与上述这些证人证词形成了共同证据,且起到了相互印证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企图,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在神秘人士寄来的这本《陷京三月记》旧书上,共有25处用钢笔作了改动,如“资财”改成了“经费”,“得便收集”改成“看到有”,改动之处的墨迹严重褪色,看来已年代久远。改动的地方都属于文字性修改,把“八股文”改为“白话文”,读起来更通俗一些,但都未改变原书表述的原意。由此推断,极有两张可能,一是蒋公榖先生在自己的“日记”于1938年8月印刷成书赠送他人后,引起了特殊的反响,有意重印,因而不仅本人作了文字的修改,而且利用特殊的人脉关系,找到了程潜、陈布雷、张自忠等11位国民政府军政要员,分别写了序、跋等,因1943年心脏病发猝死,此事一直耽误至今;二是蒋公榖有心将该书成为正式出版物,在社会上更大范围内传播,将该书连同11位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手书”,一起交给了某出版社的某位编辑,而这位编辑对该书进行了25处的文字修改,还未来得及交于作者审定时,蒋公榖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使得该书的出版拖延下来,成为今人的一个谜团。愚以为后一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迄今为止,原国民政府高层人士谴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献记录鲜有发现,以至于日本右翼势力曾据此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例如,在日本有着南京大屠杀否定派领军人物之称的原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曾说:“中国方面(国民政府)未提及大屠杀之事”(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内部版)1985年8月,第17页)。而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齐声强烈谴责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如爱国将领张自忠写道:“这是血的记录,这是的的确确的事实,这足以概括说明倭寇之残忍暴虐┅┅”。从这些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手书”中,人们不难看出,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后,原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是了解实情的,虽然没公诸于报刊。但正因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立即提出将南京大屠杀作为专案审理的诉求。
是谁苦心收藏保存了这批“手书”?为何在时隔60多年后,以一封平信的方式悄然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愚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念头。毫无疑问,一旦这些“手书”得以确认,将是屠城血证中的“重量级”史料。于是,我带领馆里的几位同事,开始了调查考证,试图找到神秘的捐赠者。
首先从邮局查起。我们去了位于鼓楼广场东南角的南京市邮政局,该局领导根据信封上邮戳的“16支”字样,断定该信是从下关挹江门邮电分局发出的。于是,我们又火速赶往位于挹江门外渡江纪念碑广场东北角的邮电分局,找到了当时分检该信件的工作人员。据她回忆,8月16日,从邮电分局门外的邮筒里取出了该信,由于信封上盖有“邮资总付”的戳子,便把它按常规做法投了出去,此外再无线索。
根据“时代超市南京店”宽大的白色信封,我们又来到了位于中央门附近的时代超市调查。超市人员说,该超市用这种信封给会员免费寄商品信息资料,而会员数量有一万多户,寄信人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根本找不到是哪一用户,再次利用了该超市信封寄如此重要的文献。鉴于信封上的字迹大小不一,笔画有抖动的迹象,“献给下关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字是繁体字,且捐赠者不清楚纪念馆馆址位置,因为纪念馆并不在“下关”。据此,我初步推断,寄信者有可能是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会不会就是当年受委托负责编辑该书的人员?如果猜想成立,他应该有80多岁高龄。那么,他为何不把这些贵重的“手书”留给子女或亲属呢?为何不公开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理的解释是,有可能老人不想让子女或亲属责怪他(她)做出如此“傻事”,而干扰他(她)捐赠给国家心意的实现。
从信封上无法寻找到捐赠者,我决定从11份“手书”考证上寻找突破口。于是,请来了一批专家为其作鉴定。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秘书长章义平从纸张和墨迹陈旧的角度,且纸张大小不一,字迹各异,认定这批手稿为原件。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多年的南京医科大学医政管理学院院长孟国祥教授,则从“手稿”用纸上考证其真伪。他举例说,白崇禧的“手稿”是写在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用笺”上的,而从1938年12月起,白崇禧曾任桂林行营主任,而朱绍良用“甘肃省政府用笺”,蒋鼎文用“陕西省政府用笺”,这些“用笺”与“手稿”主人公当时的职务是相吻合的,据此,孟国祥教授认为这是一批真迹。
为了考证这批“手稿”,我们除了在本馆查找《抗日战争大画册》《世界二战史大画册》等史料,还专程去了原“总统府”旧址,希望从近现代史陈列馆馆藏资料中,收集并核对11位原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墨迹,得到该馆刘晓宁主任等人的大力支持。我们又找到南京市公安局刑事技术科学研究所,请字迹鉴定专家进行字迹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