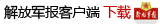2、特朗普个人因素的确定性
既定的国内外环境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设定了明确的诉求与目标,而特朗普个人的特质将直接决定着其实现目标过程中的风格、偏好以及局限性。从其成长经历、商业生涯及竞选表现观察,特朗普的“商业思维”、“军人情结”、“反建制派”倾向,以及因缺乏经验而必须经历的漫长“学习期”等因素,都将在其对外决策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首先,特朗普的“商业思维”构成其对外决策的核心理念。作为首位直接从商界步入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完全可能将其在商界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与处事方式带入内外决策。同时,特朗普在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以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位上安排商业界人士,也强化了“商业思维”在决策过程中的渗透。
“商业思维”在对外政策上的最主要体现即所谓“跨议题联动”的“大交易”倾向。正如特朗普在其畅销书《交易的艺术》中所言,“我做生意还有一条原则,就是多样化选择,我不会只寄希望于一笔交易或一种方法。……应该做好几手准备,很多生意起初看来很诱人却多以失败告吹。……我也常常准备好几套运行方案,最完美的计划也有出问题的可能,不得不防。”在“多样化选择”思路的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可能采取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施压或妥协的方式换取在核心议题上目标的实现。事实上,在其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曾经表达过在南海事务上向中国施压,换取中方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所谓“更为规范”行为的立场倾向。而在参与跨议题交易的选择上,特朗普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考量,“牵制对手,就是你手里要握有对方想要、需要、离不了的东西。……让对手知道,这笔生意可以让他得到很多好处。”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从对手的实际需求而非自身偏好出发,选择以美国可以施加绝对影响的、对手最为急迫关切的议题来充当交易筹码。
同时,特朗普的“大交易”是以“底线思维”为保障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做生意的方式简单又直接。我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然后为此不断付出,直到成功。……我是生意场上的保守派,每笔生意我的原则都是:做最坏的打算。……并且提前想好应对措施,那么好事就会不请自来。……有时候,在一场战役里,输是为了更好的赢———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外加一点运气。
此外,基于对交易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特朗普展现出鲜明的“去多边化”倾向,即倾向于美国与相关国家一对一的双边交易,从而保障美国利益最大化,而非选择需要多方之间妥协、达成均衡的多边安排。这一倾向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即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同时表示将与日本等国展开关于双边贸易安排的谈判。
第二,特朗普的“军人情结”影响其对外决策中的手段侧重。根据报道,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多次表达对乔治·巴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二战美军将领的仰慕之情。在提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詹姆斯·马蒂斯出任国防部长时,特朗普也曾评价道,“(马蒂斯)具有与巴顿最为相近的品质”。这种欣赏、青睐军人的偏好,不但表现为增加军费支出、提高军备水平、扩充军事能力等竞选承诺,也落实为在2018财年总统预算中540亿美元的军费提升。甚至军人背景的人选也在特朗普政府团队中占据了空前比重,马蒂斯是继1950年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以来首位出任防长的军事将领,而防长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同为将军背景的情形在美国政治史上也是头一遭,此外15位内阁部长中有6位具有军旅生涯,刷新了美国总统内阁的历史纪录。
特朗普的“军人情结”一般被认为源自其早年在纽约军校的学习经历。由于性情顽劣,特朗普从八年级起被父亲送入纽约军校就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段经历教会了他“严于律己……把好胜心用在取得成绩上”。在军校期间,17岁的特朗普被任命为队长,开始负责管理一些本队同学。对此,他曾回忆道,“我在军队体制内表现得非常好,我成为整个学校顶尖学生中的一员。”换言之,军校生活以及军队中的等级体制,使青少年时代的特朗普获得了成就感,并树立起他对军队以及军人的极大好感。
这种情结直接决定了特朗普担任总统后重视军事力量的倾向,而对军事力量的倚重,不但可以为应对“首要威胁”提供必要保障,也能成为达成跨议题交易的强有力筹码或所谓的“最后底牌”。
需要强调的是,按照其个人回忆,特朗普在军校期间特别尊敬一位海军军官出身的老师兼棒球队教练。而作为棒球队队长的特朗普一方面表现良好,让教练满意,另一方面却既不表现出惟命是从、也不挑战强者,而是选择自己展示出自己的强势,从而赢得了教练的尊重与真诚相待。这段经历暗示着,特朗普可能会通过采取单方面强化军事力量的方式,对包括主要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形成巨大威慑,从而维持世界对美国实力与地位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