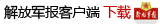第三特朗普的“反建制派”倾向塑造着其对外决策的内部生态。特朗普自竞选之初就扛起了“反建制派”大旗,其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准确地驾驭了美国民众对“建制派”政治精英极度不满的民怨情绪,甚至承接了2009年以来美国共和党内部“茶党”势力的激进趋势。这种“反建制派”倾向凸显了美国历史中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特点,即“对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认为是其代表的人们的反感和怀疑,是一种一贯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政治与政策过程中的集中体现正是对专业且具有经验的精英的高度不信任。
自当选及上台以来特朗普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反建制派”倾向。一方面,在政府团队的组建上,特朗普放弃了平衡忠诚度与专业度的惯常做法,一味强调忠诚度,在重要决策职位上排斥具有专业积累与政策经验的“建制派”人选。如此“任人唯亲”的做法,不但极大放缓了特朗普政府完成构建并顺利推进政策的脚步,还引发了某些关键人事安排无法经受媒体与舆论监视、拖累特朗普政府稳定性的窘况。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会共和党人、共和党传统智库在内的本党“建制派”势力的不满与不信任,特朗普明显依赖于身边的核心小圈子决策。这种相对封闭且又难以保证专业度的小圈子决策直接导致了诸多问题的滋生。比如,特朗普政府只能通过总统行政令方式单方面推进某些政策议程,其效果与质量明显弱于与国会合作彻底落实政策的立法方式;再如,某些重大政策(如1月27日和3月6日先后出台的所谓“禁穆令”的两个版本)明显缺乏充分评估与协调,持续引发国内外争议。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总统制的决策生态下,总统在对外决策中握有更大主动权,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以忠诚度为基础的小圈子决策,将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持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特朗普漫长的“学习期”决定了其对外决策的聚焦性、突发性与延续性。虽然特朗普曾表达过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国际局势。……花一些时间来了解国际形势,看书,并成为一个弄潮儿。……关注全球,你会发现自己能够领跑这个时代”,但这位历史上首位既不具备政府经验、又不具备军事经验的美国总统,事实上并不熟悉国际事务与对外决策过程。因此,他势必将面对与以往总统相比更为漫长的所谓“学习曲线”或“适应期”。
通常而言,由于缺乏必要的外交决策经验,新当选总统及其助手团队往往在第一任期的第一年里难以明确推动某些对外政策,而是会选择在国际事务上的更多体验、学习与适应。即便新当选者是具有类似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副总统等经历的“华府圈内人”,也难以保证其对大多数外交事务都了如指掌,更何况是特朗普这样毫无经验的“新手”。在这种情况下,新当选总统往往不得不设定外交政策的首要议程,专注于最为感兴趣或者最为重要的议题,而其他大多数外交政策将处于磨合与调整阶段。
按照总统政治周期的一般规律,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在未来至少一年中可能会重复某些特定动作。其一,外交重点可能放在其政府团队相对熟悉、而且可以尽量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并彰显执政能力的议题或领域上。从这个逻辑出发,打击“伊斯兰国”这一中东议题不但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多位军人成员相对熟悉的领域,也属于美国民意最为集中的首要安全关切。其二,在这个学习期或适应期即特朗普外交政策乃至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不排除发生某些突发事态的可能,进而特朗普政府就必须予以回应,而这种回应就存在着由于经验有限且专业度不足而导致非理性后果的可能。需要区别的是,这里的突发事态可能是外部的,即热点议题或敏感地区的突发状况,比如朝核问题、克里米亚问题、南海问题等也可以是特朗普团队成员为了追求某种政策效果而主动设定的。换言之,在特朗普逐渐熟悉外交事务的适应阶段,其核心决策成员完全可能故意引导其做出某些特定举动进而可能导致未必可控的国际后果。其三,经历一年左右的磨合和调适,特朗普政府追求“美国优先”和“再强大”目标的对外政策或战略才能成型。在国内外环境以及其他决策参与者的约束下,特朗普在某些议题上的态度完全可能明显偏离竞选论调,回归到美国某些传统立场的延续性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