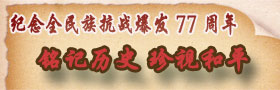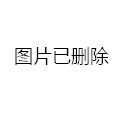
关东军占领承德后,乘势向长城一线推进。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要隘与日军浴血奋战。但因装备落后,火力悬殊较大,在汪精卫致中国驻国联代表团的电报中坦承,“一切反攻收复失地均谈不到”。4月17日,长城各口和滦东地区全部失守。时任山西省主席徐永昌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直言,“平津之失与不失”,全在于“敌之来与不来”。而何应钦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敌精我窳,终少胜算,平津若失,敌必利用汉奸,组伪政府,复演东北之故事;或移溥仪来平,再作扩大侵略,亦在意中。”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保全平津,先寄希望于“外交之救济”,走外交渠道以作“缓兵”之计。蒋介石虽然心有不甘,但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残酷现实面前,只好决定“先行缓和华北之局势”。
5月13日,日军进逼长城的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兵锋直指平津。在此情势下,南京中央政府被迫同意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5月31日早晨,天气湿热无比。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停着长长一列专列,却不见车头。列车两端为铁甲车,中间是一长串豪华卧铺车厢,窗帘低垂。这辆列车里坐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他带着中国代表团走过塘沽窄窄的街道,走到日本领事馆。在阳光下等了近10分钟之后,才被放行。
对中方代表来说,这次签字仪式处处隐含着羞辱之意——在门口迎接中方代表的日本官员个个经过精心挑选,以确保级别都低于中方代表;日方代表参谋副长冈村宁次是少将,级别也低于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中将。不仅如此,正式会议开始后,冈村宁次提出停战协定文本,声明中方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决定诺否,不许讨论,不许修改。
当时的情势下,中方无任何与对方较量的砝码。所以两小时后协定就这样一字不动地签订了。在现场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阿班记录:“签署完毕,日本人端来了香槟和葡萄酒庆祝,而这杯酒对中国人实在难以下咽,因为他们等于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本。所以签完字后,这几位中国人冒着尘土,一路蹒跚地回到专列。”
《塘沽协定》的签订,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热河的既成事实,并放弃了长城防线,将察北、冀北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军,使其随时可以进占冀察,直取平津,从而形成了对平津的战略包围态势,为日军向华北扩张敞开了大门。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大规模军事进攻,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局面。可是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多久,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华北又陷入更深一重的危机,日本方面开始着力于“华北五省自治”,力图使华北也像“满洲国”一样“特殊化”。
1935年11月1日,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35分,开幕式刚一结束,一个身着西装的青年人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应声倒下。行刺者叫孙凤鸣,曾在19路军里任一排长,后来做了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在审讯中孙凤鸣态度激昂地说:“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
那时候蒋介石面临的国内舆论压力可见一斑。可是他手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和日本相抗衡的砝码,也只能看着华北在日本的挟持下,离中央政府渐行渐远。
1935年11月25日,在北平东面相距不过数公里远的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为政务长官。这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然挂起了象征中国旧军阀的五色旗。实行了比国民政府关税少1/4的特殊关税,推行所谓“日满友好”。12月,以宋哲元为领导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中央政府随即解散北平军分会,北平实际上自此处于半自治状态。而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也正是这个背景下爆发的。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既同国民党政府有联系,又同日本有联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也给日军进一步侵入华北形成可乘之机。
华北与中央政府分离的局面已经造成,1936年日本陆军本部不失时机推出《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提出通过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支持,逐步完成华北五省的“自治”。中国驻屯军的升格、扩兵,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正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从这一点上看,“卢沟桥事变”本身缺乏“精心策划”的依据,所以一些日本历史学家一直强调“偶然性”,声称是一个误会接着一个误会,导致全面战争的爆发。对此,臧运祜也毫不犹豫地反驳:“枪响也许是个偶发事件,但不应是日军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借口。日本对华北政策早在1936年就确定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从这个背景看,即便不是7月7日,也会在别的日子发生;即便不在卢沟桥,也会是别的地点。”
牟田口廉也在“七七事变”之后获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3年以“赫赫战功”升任驻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而在1944年对盟军的英帕尔战役中,牟田口廉也带领部队遭遇惨败。被解除军职的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却未死。日本投降后在新加坡受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牟田口廉也迷恋所谓的“成吉思汗”式战术,后来在东京开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为“成吉思汗饭馆”。
对于“卢沟桥事变”,牟田口廉也曾时常对人说道:“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他在笔记中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牟田口廉也正式下令向中国军队打了第一枪,这的确是事实,不过挑起战争却非他一人之力。他只是日本战争机器上的一枚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