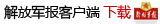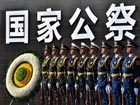每当过封锁线,母亲都要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不让我发出一丁点声音
1935年10月的湘西,霜风扑面,万山红遍。接到北上命令的红二、六军团且战且退,正在苦苦寻找一道缝隙,准备杀出重围,去追赶遵义会议之后大踏步前进的红一方面军。
偏偏在这时,经过十月怀胎的我却赖在母亲蹇先任的肚子里,迟迟不见动静。挺着个大肚子,被父亲贺龙安排在故乡桑植县南岔村冯家湾待产的母亲火急火燎,每天早晨醒来都拍着圆滚滚的肚子,对我呼喊,儿啊,你怎么还不出来啊?你爸爸就要带着大部队远远地走了,你那么不听话,让我走不能走,留不能留,扔下我们娘俩那可怎么办啊?
好像是听见了母亲呼喊,11月1日,母亲去上厕所,我竟懵懵懂懂地从她的身体里探出头来,似乎想看看她到底急成了什么样子。血泊中的母亲忘记了痛疼,脱下一件衣服把我裹了起来,让警卫员火速给父亲报信。父亲正在前线阻击敌军,最先得到消息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命令电台给前线发报:“祝贺军团长生了一门迫击炮!”
到这时,父亲才长出一口气,抽出大烟斗装上一袋烟,坐在指挥部里美美地吸起来。然后,他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和贺炳炎等战友和爱将说:“嘿嘿,我当父亲了,你们说给这个丫头片子起个什么名字呢?”副军团长萧克刚娶了我的幺姨蹇先佛,和父亲在搭档的基础上又成了连襟,他说:“恭喜,恭喜,军团长带领我们打了胜仗,又喜得千金,我看孩子的名字就叫‘捷生’吧,小丫头在捷报中出生嘛。”父亲一锤定音:“要得,孩子就叫捷生,这名字响亮!”
18天后,我坐在由一匹小骡马驮着的摇篮里,成了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一员。队伍上路时,嘁嘁嚓嚓的脚步声和嘀嗒嘀嗒的马蹄声,让我乖得不敢发出哭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躺在这样一个摇篮里,不知道队伍朝哪里走,也不知道驮着我的那匹黑色小骡马,是父亲在万般无奈中动用他的柔情,特地调来供母亲和我使用的。
父亲原本是不准备带我走的,他连寄养我的人家都找好了。是他的一个亲戚,说好在部队离开前把我送过去。但当父亲和母亲轮番抱着我赶到这个亲戚家时,一家人已吓得不知去向。还在月子里的母亲虚弱得像片随时可能飘落的树叶,这时却像母狼般地紧紧抱住了我。父亲也不是铁石心肠,看到母亲生怕失去我,他咬咬牙,说:“那就把小丫头带上吧,不过路上艰险,是死是活就看她的命了。”
我就这样跟父亲和母亲走了,跟着那串时而敲打在岩石上、时而踩踏冰雪中的马蹄声走了。每当过封锁线,母亲都要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不让我发出一丁点声音。有几次,因为母亲把我搂得太紧,奶头堵得我透不过气来,都快把我活活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