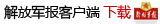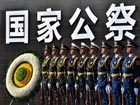陈希云叔叔看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不知从哪儿寻来一块花布,交给母亲说,女孩儿爱美呢,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
没几天,发生了后来流传甚广的故事:父亲把我弄丢了。
那是过贵州的一个山垭口,前后突然发现了敌人。父亲意识到有落入包围的危险,打马狂奔,迅速调动被挤压在山垭里的部队抢占两边的山冈。但他想不到,就在这时,我就像个飞起来的包裹,从他的怀里被颠了出来,重重地落进路边的草丛里。接下来杀声四起,红军从山垭口夺路而行,没有人会想到从军团总指挥的怀里掉出一个孩子来。
部队突围后,山垭复归沉寂,山风像水一样徐徐漫过来。我想,我落入草丛后的反应纯属条件反射,当那串熟悉的马蹄声消失之后,摔晕在草丛里的我慢慢醒来,感到周围冷冰冰的,不由得哭了起来。但我那天的哭声,是那么微弱,那么的有气无力。
山垭遭遇战后,父亲带领部队一口气奔袭了几十里。喘口气的时候,他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掏口袋里的烟斗,就像触电一般,猝然发现身上少了什么。一声“糟糕”还未出口,汗珠已滚滚流淌。当即他烟不抽,脚不歇,带上两个警卫员,快马加鞭,火速返回去寻找。
路过一片树林时,几个坐在树下歇息的伤病员看见军团总指挥驰马过来,急忙站起来敬礼,父亲的马像风一样从他们的面前刮过去。这时候,他的心里只有孩子,只有他认定丢失我的那个山垭。
跑着,跑着,父亲心里一惊,下意识勒住了缰绳。胯下的马在啸叫中掉转身子,又往回跑。跑回伤病员跟前,父亲没头没脑地问:“你们看见了我的孩子吗?”
伤病员们一愣,把刚捡到的襁褓茫然举起来:“总指挥,是这个孩子吗?”
原来,落在大部队后面的这几个伤病员,在走过刚打过仗的那个山垭口时,奇怪地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他们在草丛中找到我后,见我裹着红军的衣服,认定我是红军的后代,于是抱上我继续赶路。
“是她!是她!”父亲从马上滚下来,如同抢夺一般把襁褓搂进怀里。掀开一看,我哼哼唧唧的,饿得把手指吮得吱吱有声。
父亲的眼睛红了,两滴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
说起来,最难的还是我母亲,她可不是粗手大脚的乡下女人,而是长沙名校兑泽中学毕业的进步学生,长得细皮嫩肉。但她选择了革命,选择了我父亲,也便选择了此后遍布荆棘的苦难人生。背着刚剪断脐带的我长征,她遭受的折磨和艰辛,起码是其他人的两三倍。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一个在月子里以虚弱的身子踏上漫漫征途的产妇。
刚出发时,我还能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让母亲拄着一根竹竿走自己的路。但到了云南境内,山高路险,树杈横生,她怕剐伤我娇嫩的皮肤,用一个布袋子兜着我,挂在胸前。走那样的路,连骡马都会失足跌进深渊,她一个女人,胸前还挂着一个四肢乱蹬、嗷嗷待哺的婴儿,需要付出多大的体力和毅力!
一次,我病得非常重,两三天都哭不出来,大家认为我不能活了。建国后担任农业部部长的陈希云叔叔看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不知从哪儿寻来一块花布,交给母亲说,女孩儿爱美呢,走的时候用这块花布包她吧。母亲的心一颤,藏起花布,用尽办法救我的命。她想,女儿可是贺龙的命根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用自己的胸膛把她暖过来。即使死,也要让她死在自己的臂弯里。
万幸的是,我真是命大,几天后又能哭了,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