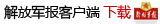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二)
如果说回老家必定要去给祖坟上坟,不如说是为给祖坟上坟必须回老家,这二者的界限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就让我将其模糊。这样有意无意地模糊做一件事儿的意义,或对一个人的重新认识,成为我生活和做事的一种习惯。有时候觉得这两件事同样重要,有时候又觉得两件事其实根本没什么意思。感觉同样重要的时候,我的灵魂还在;感觉都不重要的时候,我的肉体还在。有时我在想,这样的问题也许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思考没什么用处也不会引起人的共鸣。
车载着我——有些年带着父母和妻儿——停在一条叫做水磨河边一个叫做兴场的小站。兴场本叫复兴场,84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把整条街都冲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零零星星一些关于旧社会土匪、枪和家族争斗的传说,离兴场约五百米的河中央有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着许多鸟,但后来竟也被河水渐渐冲小冲走了,连一块小土堆都不剩下。岁月就那么轻易地流走,而一些人和往事又那么轻易地被人淡忘。父亲一路告诉我,曾经的兴场上发生的关于英雄的故事,主角是我们的祖上,他持枪在众人面前杀死了当地最大的地主恶霸,尔后从一条秘密小道逃往梁平,躲过了生死劫难。从那之后,那个地主所在的家族一蹶不振,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后人为他祭扫坟墓。
父亲一再跟我说起祖上的英雄故事,我也宁愿相信那些故事曾经真真切切地存在过,因为我从父亲的身上找到了关于英雄的某些影子。父亲是孤独的,大凡英雄都无比孤独,自种的烟草成为陪伴他孤独灵魂的忠实追随者。那种呛人的浓烟从他口中源源不断地吐出来,弥散在三间土墙房的每一个角落,往往引来母亲以及我和弟弟的责备。性情一向暴虐的父亲却从来没有因此而生怒意,只是呵呵一笑,毫不理会。许多年后,我也加入了疯狂烟民的行列,我明白了父亲心中的那些孤独,甚至从那些缭绕的烟雾中看到了父亲挑着补伞的担子行走于黔湘鄂川四省交界的偏远山寨那艰难的脚步,以及在靠手艺为生的艰难旅途中遇到的种种危难事件。那些孤独成为我继承父亲衣钵的一根红线,在我长大之后,助长了我对父亲威严的尊敬和顺从。其实父亲后来不再威严,在重庆家里的狭小空间里抽烟也小心翼翼,许多时候都打开房门自己一个人躲在楼梯间默默地抽烟,甚至是严寒的冬天。每次这样,我也不阻拦,任由他去,只是他内心的孤独我是大抵能够体会的。
那些山路成为我归家必经之路。路并不陡峭,只是湿润的空气让路非常湿滑,运气不好,碰上下雨,更是寸步难行,带着妻儿,不到两公里的山路,近两个小时的攀爬,其间五六次的歇息,终于爬上崖上,站在崖边,享受凉风习习的惬意,回望来路,竟不知是如何爬上来的。那些路在我远离他乡之前曾经让我行走如飞,哪有今日的艰难: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行李还落在父亲的肩上。我不知道是我抛弃了故乡,还是故乡抛弃了我,一步山路,竟让我吃进苦头。那个时候,我就想起父亲的一句话:你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永远不要丢掉农民的本色。重回故乡,累在山路,我不知道我的肉体和灵魂里,还保留着几分农民的颜色。
从我参加工作起,只要我回老家,祭扫祖先的事情都是我在操办,父亲甚至连问也不问一声。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他。他说,他老了,管不到这些了,这些事情就让你们年轻人去做吧。我知他不是懒散,也不是不相信祖先在天有灵,更不是有意亵渎先灵,不然,他不会在每次谈到祖先的时候眼中闪现闪亮的光芒,也不会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在整座山上去认祖坟的方位,并告诉哪一座坟是哪一位祖先。每当过节的时候,他会教我把烧纸叠成正方形,用白纸包住,这样被白纸包住的烧纸叫做悱纸(土话,音同“飞”,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fēi字怎么写,查了新华字典,觉着“悱”字可以较为准确地表达阳人怀念先祖之意,于是就用了它),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故显考何公讳XX老大人……”、“故显妣何母X(姓氏)XX老孺人……”等字样,然后把“悱纸”依祖先的辈份高低依次排放在方桌最北端,在“悱纸”前摆放酒肉饭菜,点上桐油灯。父亲端起酒杯,面朝北方,用忠县土话大声叫道:“各位老辈子回来吃饭罗,没有请到的老辈子莫怪哈,请原谅晚辈的疏漏,知道今天过年,也莫客气,也莫生气,自己跟着回来一起吃个便饭吧——”然后恭恭敬敬鞠三个躬,从左到右,朝地上连酒三杯酒,恭迎祖先回家过年的仪式就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和弟弟才可以随便拿东西吃,不然,按照母亲的说法,那是对祖先的大不敬。
当时我并不能够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更多的时候是觉得好玩,而威严父亲的毕恭毕敬毫无疑问深深影响了我对祭祖仪式的思考,直到后来父亲不再操办祭祖仪式之后的很长时间我才逐渐明白过来。那是像乌云背后广阔蓝天一样深邃的孤独:子孙在祖辈的庇护下渐渐长大,而长大后当一代代祖先一个个离去,接踵而至的生活上的艰难必然导致精神上的困顿,想要找到精神的依靠和某种力量的鼓励来支撑生存的勇气,最自然而最捷径的方式就是寻求祖先的护佑。父亲也不例外,在几十年艰难生活中四处漂泊求生,撑起这个家,他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帮助他。然而没有,分家时只分到两只罐子一个装粮食的小木柜子,兴家立业全靠自己打拼。那种孤独,那种无助,在深深的黑暗中抽着旱烟想着心事的父亲,我却从来没有见他流过一次眼泪。他以一位英雄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并以其智慧有惊无险地经营着这个家,使周围的人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轻视过,即使小时的我身体无比羸弱,但也会得到大人们的疼爱,并不曾被欺负。
许多次回家都逢上阴雨天,雨雾笼罩着雁架岭的山与水,房与树。泥泞的道路一步三滑,其中有三次带着儿子回家。牵着儿子,或背着儿子,走过湿滑的土田坎,小心翼翼地迈开脚步,深怕一不小心和儿子一起掉进寒冷的冬水田里。儿子倒显出不害怕的样子,反倒转过身来叮嘱她的妈妈一定要小心。我不知道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像儿子一样对母亲这样的担心,也许在所有儿子的心里,母亲是最需要照顾的,而父亲永远是坚强的、智慧的,永远不需要担心。
其实对父亲在很多年里都有很深的误解,直到父亲在我尚在学业时从悬崖上不慎掉下,摔断了三根肋骨,三根肋骨错位,但父亲竟然在二十六天内坚强地站了起来,让我对父亲的看法有了改变。父亲暴躁的性情就像雁架岭的狂风暴雨,想挡也挡不住,时常会刮得我头晕目眩。无论我犯没犯错误,记忆中的童年时常被父亲一顿粗暴地毒打,有一次被打得鲜血直流。父亲见不得我软弱,心中有了委屈,从来不敢告诉他,怕他说我不勇敢不坚强,更多的委屈装在心里,经常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泣。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不够坚强,而父亲的粗暴的方式或多或少改变了我软弱的个性,当我走出校园远离家乡面对诸多的困难,能够勇敢地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