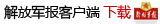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四)
几乎很少的时候我会去在意自然环境的变化,或者这些变化对我的心情的影响。但这丝毫不影响关于雁架岭给我的童年生活的记忆片断。有人说时光的流逝会消磨一切事物,而对于我的内心而言,有些片断像运用蒙太奇手法将生活经历精心剪辑然后在无数次梦里翻来倒去地放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竟越来越清晰。
常常想起从前的割草生活。家养一头大母牛,甚至会带着一头小牛犊,只为了春秋两季的耕田。父亲是那么倔强的一个人,从来不会去欠别人家什么,哪怕向旁人家借牛耕种这样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论再辛苦,都要自己养头牛,养得肥肥壮壮。父亲常说,牛和人一样,是有感情的,只要你给它草吃,吃饱,它就会在农闲季节赶了劲地长膘。等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它就会给你十分的卖力。
家乡山高路险,且养的是大水牛,不善走山路,除了山下河边的人家会让孩子放牛,岭上人家的牛大多割草回来喂养。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割草的活儿就由母亲承担。母亲通常在山上某个地方干活,见时间不早,放下手中的活儿开始割草。印象中,母亲是很会割草的,即使大冬天,她总能从枯草飞尽的山坡上割到满背蒌嫩嫩的草,骄傲地背回家,别人家看到她割到那么多草,总是问她割草的地点,母亲总是笑而不语。其实别人去她割草的同一地方,也不一定能够割到。
割草是需要耐心的。那种耐心需要对割草当成事业来做,不只是完成任务,不只是喂养一头牲畜的简单需要。不仅要对家里的每一头牲畜怀着深厚的感情,而且要对割草这种简单的劳动怀着无比热爱的心情。在这些简单劳动的背后,似乎蕴含着一个关于生存、美和个性品质的深刻道理,它隐藏在我的乡土的山山水水和张张淳朴脸庞的憨厚笑容中,你必须细细体会才能够深切感受,并用一生的时光去学习,以一颗真诚的心去领悟,还要付出真实的艰辛劳动才能收获其中的快乐。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对人生的认识就是从割草开始的。家家户户都喂养牛,岭上的草只要一长出就被人早割光了。遇到庄稼正茂时,又害怕秧田里打了农药,田坎上的草是万万割不得的,不然会毒死牛,邻居家的一头牛就是因为吃了染过农药的草而不幸归西,那样的事情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是绝对承受不了的。要割到草,得沿着无数条延伸到坡上每一个角落的山路,下到岭去,在离坡上种了庄稼的土地远一些的荒野去割草,那里才有足够的丰茂的草装满你的背蒌。而这样的地方往往离家就远了,通常会有两三公里的路程,草割好了,还得背着草,沿原路往岭上爬。空背蒌去时走半个多小时,背着草回家得走上一个多小时,大汗淋漓,疲惫不堪。如果是下午,放下草背蒌,已是繁星满天,把草抖散,松散地堆放在牛圈旁,熊抱一怀草,丢给牛,看着牛近乎疯狂地吃着,这才满了意。
割草看着是个粗活,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一招一式,都容不得半点大意。你得左手抓住草,草得不多不少,多了攥不住,少了费工时;抓草的手要不松不紧,当镰刀割下草的时候草才不至于脱手。右手拿着镰刀,将锯齿一样的刀锋顺着草的根部从右上至左下划过去,左手轻轻地往左上方带,草才会脱离地面紧攥在你的左手中。并不放下刚才割下的草,仍旧攥在手中,接着割下一次,等到手攥不下了,才从手中的草里选一束长的草,撩出来将草挽成一把,简单打一个结,放在自己能够记住的地方。不然割一背蒌草,漫山遍野跑,回头却找不见草把,那就亏大了。我在山上割草的时候,就经常发现有挽得好好的草把还躲在某个角落,就会哑然失笑。
山坡上什么地方都长草,平地上、沟坎上、树林里、刺茏中、甚至悬崖上,只要有草的地方都会有人去割。为割到鲜嫩而茂盛的草,有的人会爬上悬崖去割一种叫巴茅的草。巴茅的叶片修长,边缘长满了锯齿,稍不注意就会划伤手。我胆儿小,一般只在平地上,至少不会去有掉下悬崖危险的地方割。其实很多时候我是很羡慕那些敢于到悬崖边上去割草的人,但我一站到悬崖边上就发晕,更别说通过艰难的攀爬到达茂草所在的狭小空间。不过,我有自己的办法,总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发现长得茂盛的草,而且手式也比别人快,所以总能很快割满一背蒌,然后坐在一边休息,看别的人还在忙活,心里就特别高兴。
划伤手是难免的,至今我仍在手上珍藏着大大小小几十道因为小时候割草留下的伤痕。每每洗手的时候,看到那些伤痕,心里总是想起多年前的割草生活。有一次我半蹲在地上专心地割着,未料一块隐藏在草丛中的坚硬石头将镰刀重重地弹了起来,撞进跪在地上的左膝盖上。哎哟,当时那个疼啊,钻心的疼痛却立刻麻木。我卷起裤腿,看到膝盖上鲜血直流,白花花的肉翻卷出来。一旁的小姑见状,并未吓着,从近旁的石头下抠下一砣石花,盖在伤口上,过了一会儿,血就不流了。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那种长在石头上的白色粉末还可以止血,那不能不说是大自然的一个造化。
其实大自然的造化远不止这些,远离他乡的游子一生,其实一直都在享受着自然给予的恩赐,更多的只是缺少发现,包括等待。想起那些等待的日子,我不知道算不算幸福,但简单地等待,对生活没有奢求地等待,没有过多欲望的等待,会让人心境平静。就像我在七八岁时,割完草,伙伴都走了,我个儿小,力气不足以背动一蒌草,只能在幽深的山谷中等待母亲忙完坡上的活天黑后来接我。奇怪的是,我现在已记不起那个时候是否害怕,但还记得起无数个太阳落山后的山林各种各样的鸟儿此起彼伏的鸣叫,大概是鸟妈妈们在呼唤自己的孩子回家。我守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想着妈妈一定走在向我的方向的路上,她一定也在担心我是否害怕。至于她是否问过我害怕不害怕,我也记不清了,记忆中她并不曾责备过我,也不曾夸赞过我,即使在乡亲们夸我懂事时她也不曾附和别人的说法,反倒当着别人的面说我还不够听话,但我分明看到她脸上满足的表情。于我而言,她那种表情,是我十分愿意看到的,是我很小的时候所能够理解到的内心孤独的母亲抱有的全部希望。到我大一些,长到力气足可以背动自己割的草时,即使走得慢些,落后伙伴们许多,即使很累,我也不愿母亲去接我了,我觉得那是可以帮她干的最大的事情。
休假归队有时候会从重庆经成都回到拉萨,定会坐公交前往成都。那路公交每次都会经过一座人行天桥,每次我从那人行天桥下经过时,总会看到母亲站在天桥上向我微笑着挥手。母亲是不善言语的,但她那微笑和挥手的动作却一直向我传递着某种关于坚强和牵挂的强烈情感。母亲,母亲——我在心底这样默默呼唤着,希望这样的呼唤能让母亲体验到一个军人、一个游子对她的如同她对我的毫无保留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