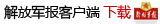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五)
关于故乡的记忆我是害怕淡忘的,只因为我所熟识的长辈一个又一个在电话里或在我能够听到的鞭炮声中离开这个尘世,但没有一个是我所亲眼见到的。死亡,正如当我战斗在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时所能感受到的那样,无数次我清楚地感受到长辈们离开时候的恐惧和快乐。久病之后生命的悠悠而逝,或是在任何人不经意的时候一颗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每个人离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多年之后却同样时不时勾起忧伤的回忆。
生命离去并不可怕,爱,却赐予生命延续的伟大力量,这也让后人们回忆过往人物的最大理由。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叙述关于长辈们离去的悲伤故事,那将是无数个长篇小说都不能穷尽的平凡阐述。但我可以简要地把他们站在我梦中的形象作一描绘。
记忆中最早离开我的应该是三姨,如花似玉的年纪成绩十分优秀为人十分礼貌的三姨患上了肺结核,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一年多后静静地闭上眼睛,她最后的遗容那么安详,除了脸色苍白,不像是生过大病,倒像是绝世美女安然入梦,只是那梦不再醒来。出殡的那天村里所有的人都为她送行,哭声连成一片。从那之后我知道了一个人还可以为一个与自己不太相关的人流那多么眼泪。
三姨过后就是奶奶。奶奶是在春天去世的,也是肺病,但病了很多年,去世前还在操持着家务,而那些烦琐的家务爷爷是从来不管的。奶奶其实与我感情并不是特别亲的,但她的去世却成了我怀念中最为伤心的部分,只因为她是我的奶奶。她一生为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以及不管家务的丈夫操碎了心,我的母亲像极了她,能干而诚实,沉默而坚韧。下葬的那天早上下着大雨,我与家人(除了爷爷)为她跪行,一路泥泞污了全身但却掩不去心中的悲痛。如今我还保留着她的照片,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活像罗贯中的《父亲》那张脸一样沧桑,近二十年过去了,仍让我的内心阵阵悸痛。我不了解她,就像她对我并不抱什么期望。我宁愿她活到现在,能够自豪地对世人夸赞自己的孙子,也让我能够有机会做些尽孝的行动,于我于奶奶这都是一个遗憾。后来我告诉弟弟和堂弟,我们一定要加倍地努力,做些出息的事情,至少可以安慰她的在天之灵。
外公是在瘫卧在床两年后一场奇怪的火中被烧死的,火势现场除了他及身下卧椅被烧焦,连他身上披的用作保暖的老式军大衣都被丢在一旁。那时候舅舅的儿子我的表弟正在上大学,又没有经济来源,十分贫困,还要为他治病。我猜测他是对自己长年卧床的厌倦并对治愈彻底绝望,之后,实在不愿意成为家庭的负担,便近旁靠墙的电源接在自己身上被烧的,而走之前还不愿给家里的东西造成损失。在出殡前夜的乐鼓声中我在前来参加悼念仪式的乡亲面前这样去解释他的离去:一场火涅槃了他的灵魂,既为重生创造了机会,也为后人带来了希望;那火一样的飞升,告诉我们该如何光明磊落地做人,又该如何对生活充满激情,并为梦想做毕生付出,永不放弃。外公走后,外婆的精神每况愈下,痴痴呆呆一年便随外公而去了。外公去世时,我的父亲母亲、大舅舅妈、二姨二姨父、幺姨幺姨父及我和表弟都在家为他送葬,可怜我的外婆走时只有我的父母和舅妈、表弟为他送行,舅妈、二姨二姨父、幺姨幺姨父都在广东打工没能及时赶回,外婆临走时意识突然非常清醒,流着泪说让他们别回来,怕花路费,还要辞工,怕再回去时找不到工作,大家挣点钱不容易。而我远在西藏,也不能回去,只能每天打电话向父亲了解情况。舅妈身体一直不好,那段时间精神几近崩溃,只有父亲回去帮着料理外婆的后事,我也只能是寄些钱过去。外婆的去世让我知道,不仅要考虑故去人的后事,更要照顾未亡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倒是母亲两次回老家为自己的父母送葬,精神也险些垮掉,外婆去世后母亲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输了好久的液才有些恢复。
近几天父亲回了趟老家,说爷爷身体尚康。近八十岁的老人一个人生活在农村,并非父亲不孝,也并非我不孝,只是条件实在有限,爷爷是理解的。我不知道爷爷还能够活在这个世上多少年,每次回老家爷爷总是舍不得我走,每次都要做饭给我吃,而我怕麻烦他,不让他做,只叫他随我去舅妈家吃饭(舅妈家离我家并不远)。我搀着他走过泥泞的田埂,生怕他跌倒,而他却总不愿意我扶他,说现在还走得动。每次都给他留一点儿钱,他总是很幸福地接过钱,也有些不好意思。我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地活着,活到看到可以用到弟弟孝敬的钱(弟弟还在读书,尚未毕业),可以看到弟弟娶回媳妇生下第二个孙子,活到我有一天离开部队回去农村陪他照顾他。这些话他一直记在心里。每次离开的时候,他都问我什么时候能再回去,但我无法回答他,只说好好活着就行。去年听说我要回去,前有好几天,他拿着长竹竿到果园里打了一大篮蜜桔,都是为我和我的儿子准备的。当儿子叫他“祖祖”(老家对曾祖父的称呼)时,他笑灿如花,高兴得不得了,走时还拿出一百块钱要打发给儿子(老家把给压岁钱叫打发),被我拦了下来。我站在旁边也很感动,我知道,对于一个老人而言,莫过于看到儿孙满堂。虽不能绕膝,但毕竟香火有了传承。所以我去给祖坟烧纸放炮的时候会带儿子一同前往,并让他跪下。儿子倒也懂事儿,顺从地跪在祖坟前,磕三个响头。这是我第二次带儿子回家,第一次是他四个月大的时候,这次回去他已近八岁了,也算是认祖归宗,下次回去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希望等他长大后,能知道自己祖籍在什么地方,那里都有些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总得有自己的根。
风在记忆中那么猛烈地刮着,很多时候我并不清楚风的思想。离开故乡太久,悲伤太久,虚伪太久,而时光已不再回流。一位朋友说我不再像从前一样从容和青春,我知道,记着每一次伤感,以及每一缕风的疼痛,脸上的皱纹也许就会增添一缕。雁架岭,在我心中艰难地活着,同我一样,一直在试图去铭记什么,忘记什么。我这样告诉自己,如果不能忘记,那就把它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