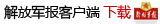老宅
■李西岳
我当兵40年,最放不下的是老宅。
老宅给我的记忆是原始的,长久的,也是零碎的,无序的。若干年,我一直没为老宅留下任何文字,不是才思的枯竭,也不是记忆的模糊,而是缺乏足够的勇气。
我们家的老宅在老家一带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属于很平常的一座农家宅院,平顶红砖,且里生外熟,即内墙为坯,外墙为砖,老家人戏称,驴粪球子外面光。不管怎么说,那年月,有这么一座宅院,就算是有些体面了。
这些年,我每年都回家一到两次,但每次都不去看老宅,我知道,我一直在躲避老宅带给我的复杂记忆和精神纠缠。
这次,我狠狠心去见老宅。
走进老宅,我的心是颤抖的。老宅大门朝北,这与中国乡村坐北朝南的风水习惯基本相悖,我不知道当年是怎么形成的。两扇大门破旧不堪,门楣上的倒贴“福”字依稀可辨,一把锈透的旧锁还形同虚设地挂在门环上。穿过一条门洞,便正式进了宅院,因长年累月无人光顾,院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多高,还有一些果树,有枣树、梨树、杏树、桃树,品种繁多。不大的院子,被这些杂草果树挤得密不透风,无路可行,仿佛进入了非洲的原始森林。我拨开杂草树枝,好不容易才看到门窗。此时,我清晰地看见,窗户是纸糊的方格窗棂,有树枝影子婆娑掠过,摇曳着久远的岁月,唤醒着我的记忆。屋门是两扇对开的,且宽窄不一,破碎的玻璃,弧形的裂痕,两扇门之间的蜘蛛网,编织着平凡的往事。进得门来,是外间屋,也是厨房和餐厅。虽然屋内满是灰尘,黑黑糊糊,但那风箱、木锅盖、面板,锅碗瓢盆,地上坐的蒲团,房梁上挂着的干粮篮子,依然按原有的秩序陈列着。细看一下用砖铺成的地板,还有能辨认出来的双“喜”字样,那是爹当年的杰作,在别人家未曾见过。回想那些年,尽管日子过得清苦,但我们进门就踩着喜字,命应该还是不错的。
撩开门帘进入西屋,这是爹娘的房间,带补丁的炕席还在,爹娘盖过的被褥还在,扫炕的笤帚还在。我还看见,窗台上有一盏煤油灯,是玻璃制成的,当年,在没电的日子里,娘和姐就是在这盏灯下为全家人做针线,我也凑到灯下看书或做作业。我更记得,我当兵走的头天晚上,娘一只手端着灯静静地看我,一只手轻轻梳理我蓬乱的头发。回想起来,那应该是一幅很浓重而温馨的油画。我更记得,娘得病卧床之后,我每次回家,她老早就凑到玻璃窗底下等着迎我,我走的时候,她又凑到玻璃窗底下目送我,我经过窗户的时候,正好看到她那张消瘦的脸和那双挂着泪滴的眼睛。那一刻,心是颤巍的。
1999年4月9日,是我这辈子最伤心的日子,我接到娘病危的电话,赶回家,娘已安静地躺在灵床上。其实,家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人就没了,爹怕我路上着急,才不让跟我说实话。那一回,我几乎把泪水哭干了,但圆了坟,没烧头七,我就匆匆赶回部队。我正在为央视一部叫做《中国军队》的电视片撰稿,任务急,不容我在家久留。又到腊月二十八,我像往年一样回到老宅,再经过窗户的时候,却见不着娘了,走的时候,也见不着玻璃底下那张消瘦的脸了,我感觉自己的心猛地向下沉了一下。这也许是我这些年不敢见老宅的根本原因。
尽管我在触摸老宅的过程中有些惊慌心怯,但还是壮着胆量在帽盒里搜出了十几封信,都是我写的,其中就有娘去世后,我安慰爹的信。那封信很长,有8页纸,再读一遍,我发现自己当初不该用那些动情的话安慰爹。家里人跟我说,娘去世的时候,没见爹流泪,看了我的信,倒是泪流不止,好几天缓不过神儿来。这说明,我这个儿子也不算聪明人,用当作家的文字赚取了爹的眼泪。我把那些信件悉数收了起来,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进老宅了,我受不了这种折磨。
东屋给我的记忆更是幽深而清新的。我很小的时候,就睡在这里跟爷爷奶奶做伴,后来我娶妻生子都是在这间小屋,再后来,小弟也曾把这间小屋做过洞房。现如今,这间小屋还是老样子,一个大土炕,一个水泥做的大躺柜。再无它物,我当兵后,每年回家探亲都住在这间小屋,直到娘过世,爹搬到弟弟们家。
爹是2005年搬出老宅的。那一年,他83岁。娘去世之后,我就劝他离开老宅到两个弟弟家轮着住,生活起居有个照应,但爹不答应。他说,只要自个儿能动弹,就不跟人过。这期间,他来过几次北京,每次不超过半月就嚷嚷着要回家。回来还是住老宅,无论别人怎么劝,他一意孤行。据说,搬出老宅,是因为他独自饮酒从凳子上摔下来了,脑袋磕了个包,这才在叔叔的极力劝说下,搬出老宅。爹搬出老宅之后,刚开始他还回去收拾一下院里的果树与杂草,再后来便力不从心了。
因为没人居住,长年累月,风吹雨淋,无人经管,老宅的自然损坏程度日趋严重,先是墙头被雨水冲倒了,再后来,西屋的房顶塌了,屋里露了天。爹让弟弟们管一管,可他们没去管。他们说,房子老了,屋里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早晚是塌,管它干啥?
大弟对我说,东邻想把老宅买走,与他们家的院子合为一体,出价还不低,他没答应,也没与爹商量,估计爹也不会答应。我也说过,给多少钱也不能卖,留着是个念想。关于对老宅的处理,两个弟弟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没什么好主意,推倒重盖,那还叫老宅吗?可这么自然地保存下去,万一哪一天坍塌了,成了残垣断壁,老宅不也成遗址了吗?
老宅让我很留恋,也让我很纠结。
人的感情就是这么复杂,我当初出来当兵,就是为了离开老宅,去寻找外面的精彩世界,而在外面混了一些年头,或者混出了一些名堂,就又格外怀念起老宅来。仔细地梳理一下,实际上,自己的成长,或者成才,应该是与老宅密切相关的,老宅作为我的精神家园,心灵之所,对我的精神激励是潜移默化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军人,要么战死在沙场,要么回到故乡。作为和平年代的军人,没有战死在沙场的机遇,那我们迟早要回到故乡,回到老宅。至少这是一种精神轮回。
老宅是我的情之所依,根之所系,魂之所驻,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古城古镇古屋比自家的老宅更亲切亲近,也没有任何一个物件比老宅更能直通我的血脉,直达我的心灵。
常年在外,年头久了,会想家。回老家,一是看老人,一是看老宅。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知道,按自然规律,老人不会常在,老宅不会常在,包括我也不会常在,什么都会变,唯独亘古不变的是拳拳之心,如何也走不出老宅。
(《解放军报》2016年06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