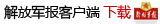2004年7月,贺捷生的母亲以96岁高龄在北京去世。贺捷生说自己能告慰母亲的是母亲对围场的遗愿,几年前就实现了。今天出版的《解放军报》长征副刊版刊文《母亲的流金岁月》,作者贺捷生在文中回忆了母亲与围场的那些往事。

贺捷生和母亲蹇先任。(资料照片)
母亲的流金岁月
■贺捷生
1946年4月的一天,我母亲坐着一辆木轮车,从热河去围场。赶车的是个老大爷,受命来迎接新上任的县委副书记,想不到坐在他车上的,却是个文文静静的南方女子。那时我母亲面色白净,目光温润,娇小的身体裹在一件腰身大口袋也大的黄色大衣里,头上戴着一顶旧棉帽子,两只护耳翘了起来,像鸟儿飞翔时展开的一对翅膀;尤其,她还带着队伍上相当一级军官才有资格佩戴的那种盒子炮,枪把上系着的红绸,像一团燃烧的霞光。赶车老人猜不出我母亲的年纪,但他怎么看我母亲怎么不像一个当官的人。车刚上路,老人好奇地逗我母亲说,这位大姐,鬼子和汉奸都打跑了,你去围场打什么呢?母亲扑哧一笑,说:“我打国民党。”
母亲那年37岁,化名黄代芳去围场做群众工作,但此时她已经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她17岁在长沙读书时开始从事地下斗争,18岁在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加入共产党,20岁在湘西参加红军并嫁给我父亲贺龙,26岁带着刚出生的我参加长征;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她28岁,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被派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工作和学习。当她1943年历经千辛万苦,从西伯利亚经新疆回到延安,她日夜思念的孩子却杳无音信。当时,人们担心她受不了这种打击,说不定会精神崩溃,会疯掉。但她不仅没有精神崩溃,而且更像一名战士站在了战斗队伍中。面对人们投来异样的目光,她淡然一笑,因为她心里最清楚,她是来革命的,而不是为了别的。母亲意识到此后的路必定荆棘丛生,坚决要求往前线走。她想,从湘西到陕北,从中国到苏联,再从苏联回国,那么艰难的路都走过来了,那么多的好同志牺牲了,我这条命,从此彻底交给这场即将到来的祖国的解放战争。
母亲通过中共热河组织部主动要求来围场工作,最直接的原因,是热河省医院出现大批伤病员死亡的事件。这家医院是从日伪手里接管的,许多伤病员莫名其妙地死亡,使人怀疑医院里存在暗藏的敌人。正担任冀热察辽军区政治部保卫科长的母亲闻讯去调查,没抓出暗藏的敌人,却发现医院条件简陋,人手紧张,管理非常混乱,有些重伤员送进去得不到有效治疗,只能眼睁睁死去。
从医院回分区组织部的路上,母亲心情沉重。她意识到,医院出现的问题原因在于形势发展得太快,地方特别缺干部,急需派人下去发动群众,做好支援部队工作。但是,当她决定亲自扎下去时,组织部领导为难了,说首长啊,你是经历过长征的人,又是……实话对你说吧,现在分区的管辖范围,只有围场缺个县委副书记,可那儿太荒凉,太艰苦,职务又偏低,谁忍心让你去呢?还是等等吧。母亲说,还等什么?我也不计较职务高低。既然围场需要人,我就去围场。
当时抗战结束刚8个月,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开始陷入僵局,两党两军必有一战已成为共识。像母亲这样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已经预感到战争即将到来,因此稍有风吹草动,她就像一支箭那样把自己搭在了弦上。
县委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当母亲到达围场县城克勒沟时,县长张静之和比她早几天调来的县委书记王克东,正带着县支队在乡村减租减息,动员群众发展生产,做好打仗的准备。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我党正在东北采取寸土必争的策略,每天都有干部从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经围场向东北开拔,需要县委派人护送。县委书记和县长见到母亲,喜出望外,说,黄大姐,你长期在延安八路军政治部和军政大学工作,各地的干部都认识,护送干部过境的任务就由你来负责吧。
母亲自然不会推辞,在她到达围场的当天,便骑上一匹叫“赛围场”的白马,开始去迎送过往干部。
骑白马,挎双枪,当我37岁依然年轻漂亮的母亲,在当年皇帝围猎的土地上,把党的一批批干部不知疲倦地送往东北时,她骑在马上的那副飒爽英姿,从此便像故事传说那样留在了围场人民和她的后辈们心里。几十年后说起这段岁月,她神采奕奕,依然沉浸在对当年战斗生活的痴迷中。母亲说,那些日子她披星戴月,风雨兼程,但她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活得特别充实。每当红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她在洒满金辉的原野上策马前行,风吹动着她齐耳的短发和手枪把上的红绸,就像一团火奔向太阳。
母亲少女时代在省城长沙兑泽中学读书时,幽静多思,文采飞扬,向往未来做一名中小学教师,或当个作家。长征后到了莫斯科,读了大量高尔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苏俄作家的作品,曾萌发用自己的笔抒写战斗历程的美好愿望。但因为经历过太多苦难,有太多的人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这使她变得沉默寡言。到了围场,这种充满激情的战斗生活让她精神焕发,变得像过去那样年轻、快乐,那样渴望经受暴风雨的洗礼。
经母亲护送的那些干部,有宋任穷、黄火青、段苏枚,还有长征期间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工作学习时的老战友、老朋友,她上抗日军政大学时的同学和当军政大学老师后的学生。她晚年回忆说,接来和送走这些干部,每次都像亲人重逢和道别,既高兴又依依不舍。把他们安顿在克勒沟县委简易招待所住下后,众人围着噼噼啪啪烧红的炭火,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天就亮了,然后又迎着黎明的曙光,打马上路。想到他们去东北,是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和沈阳那样的大城市,吹响解放全中国的号角,母亲的心里敞亮极了,就像一座房子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了。解放后,在某个会议上或某种场合见面,这些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会远远地走过来,向她致意并表达感激之情。
不久,东北的许多城市被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国共两党大决战宣告开始。大战将至,县委紧急发动群众抢收秋粮,坚壁清野,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去和糟蹋;着力整顿县支队和区小队,完善各地武装力量。农历十月的一天,黄火青同志北撤再过围场,正在孟奎区开展工作的母亲接到县委的电话,回县里向这位同时期去苏联的老上级汇报工作。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母亲才离开半天的区公所被一伙国民党匪徒包围,除少数几个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了。第二天母亲飞马赶回孟奎,看见头天还跟她说说笑笑的队员们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屋子里,墙上溅满鲜血,痛心疾首,泪水潸然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