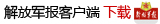王愿坚
一
人民军队是我的家,莒南人民把我养大成人。
战火纷飞的莒南,是人民子弟兵奋勇抗战的战场,也是山东的文学家、艺术家纵情驰骋的文学疆场。但对我来说,那里却是我含着奶头、吸吮着乳汁慢慢长大的一个摇篮。莒南的青山绿水、人民的恩情和军队大家庭的爱,把我这个孩子养大。
记得那是1944年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一个月明星稀的黑夜。我和我的弟弟告别了当了6年亡国奴沦陷的家乡,跟着山东军区敌工部的老孙,踏上了走向抗日根据地的征途。
7月的夜晚是美好的。我们穿过刚刚秀出穗的谷地,穿过含苞待放的豆棵子,在庄稼地里疾步穿行,一直向西。整整70里路,走了一个通宵,等到启明星亮起来,东方现出了鱼肚白,领着我们走的老孙同志突然喊了一声:“你们看吧!”我抬头望去,在一个高高的岭头上,一棵大榆树的上头,飘扬着一面鲜红的红旗。我明白了,我离开了屈辱的沦陷区,走进了一块光明自由的天地——抗日根据地,我参加抗日战争了,我终于成了一个抗日的革命者!
我和弟弟被安置在县委招待所里,住了3、4天,没有人来。我们弟兄两个等得不耐烦了,决定去找领导同志,问我们的工作问题。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和弟弟走进了县委宣传部部长王伯泉同志的办公室。我站在他的桌旁,弟弟王玉坚躲在我的身后,在肩膀上瞪着一双大眼睛。看见我们,王伯泉同志抬起头来问我:“干什么?有事吗?”我壮着胆子回答:“伯泉同志,我们是来参加抗日的,什么时候给我们分配工作呀!”王伯泉同志摸着他那短短的头发,挠了半天,突然问道:“你们能干什么?”我说:“抗战打鬼子,我们什么都能干。”王伯泉同志摇了摇头:“不!抗战,打鬼子,有这个心是好的。可是要打仗,要革命,那得学本领呀!”我愣了,弟弟也愣了,我们瞪大了眼睛,望着伯泉同志那个光亮亮的脑门,纳闷:抗战打鬼子还要学习?
王部长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严肃地说:“是,革命是要学的。你们年龄还小,将来有很多事情要你们做。你们现在还不能顶一个人用,先去学习吧,学到本领,将来工作有你们做的。”弟弟大胆地问:“我们到哪里学?学什么?”伯泉同志说:“这个已经有安排,你们到山东军区,或者进抗大,或者进滨海中学,先学习,然后领导分配你们适当的工作。”我又问:“山东军区在哪?”王伯泉同志略略想了一下说:“现在军区在莒南县,距离这里有200多里路。”“我们怎么去呢?”我有点发愁了。伯泉同志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好办,你们两个小孩子吗,贴张邮票,就寄去了。”他大概看出我们有疑惑,就开玩笑地说:“反正你们的姐夫是我们战地邮政总局的局长,邮票由他出。”
当天晚上,我们躺在招待所的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弟弟趴到我的耳边小声问道:“五哥,把咱们寄去,那邮票贴在什么地方?贴在脑门上吗?”这个问题,我也难于回答,我说:“管他呢,总归是有办法。”果然,第二天下午,有一个五大三粗的同志,推开房门进来,大声地叫道:“哪一个是要到山东军区参加革命的小王啊?”我们两个异口同声:“我就是。”那个同志告诉我们:“我是战邮总局的武装交通班的班长,我姓周,你们叫我老周好了。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们的邮件,收拾一下,明天动身。”我们弟兄俩相视一笑:我们两个大活人,居然变成了“邮件”。
第二天一早,老周同志带着3个交通员来了。他们每个人带一支步枪,肩上还背着一个沉甸甸的邮包,老周随手把两个小点的邮包交给我们,并斜着绑到我们肩膀上,一边绑,一边交代:“这是平信,由你们两个背着。要件、密件我们背着,跟着我,我们走,你就走,我们停,你就停。”我们点点头,老周认真数了几个同志肩膀上的邮包,把我们两个肩膀上的邮包也算上,“1、2、3、4、5、6”,然后指着我们的脑袋说:“7、8。”从这时起,我们便成了他的第7个和第8个“邮包”。
我们两个长着腿的邮包,跟着邮政总局的同志,上了南下的路。
走了一天又一天,走过了洪林子,穿过了石沟崖附近的封锁线,经过夏庄,一直走到了莒南县,最后在一个大庄子上停住了脚。大约是第5天的下午,我们走进了山东军区的驻地,莒南县的坪上,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见到了敌工部的赵干事。
赵干事名字叫赵东杰,大个子。他热情地拉着我们两个的手,问这问那,问我们会不会唱抗日歌曲。我们当即唱起《我们在太行山上》,还没有唱完,就被进来的周班长报告声打断。周班长多少有点不耐烦地指了指我们两个向赵干事说道:“你收到邮件,还没给我打收条呢?”赵干事笑了笑,撕下了一块纸,拿起笔写起来。我凑过去一看,他写的是:“兹收到,参加革命的小鬼两名。”签上年月日,盖上图章。赵干事一边把收条交给周班长,一边笑着对我们说道:“看见了没有?我已经把你们收下了,你们从此就进了革命的怀抱了。”
革命的怀抱,多么新鲜的字眼,多么富有感情的词句!确实是怀抱,无论从广义上讲,还是从狭义上讲,都是一个温暖的怀抱。
3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赵干事领着我们,来到了坪上村前的大河滩。河滩上用土堆起了一个高高的舞台,挂上了幕布和汽灯。我们坐在舞台前面,沐着盛夏的晚风,瞪大眼睛,盯着面前的舞台。台上正在演着苏联殊科写的著名话剧《前线》。那些化装成高鼻子的人,穿着洋衣裳,还有那些看不懂却又很新奇的苏联的战争生活,可把我们这两个从敌占区刚刚跑到根据地的孩子给迷住了。
刚刚看了个头,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军人走到我们中间。他推开别人递给他的一个小板凳,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我和弟弟揽在自己的怀里,小声地问我:“你是这村的吗?”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山东诸城的,刚刚来参加革命。魁梧军人说:“好,这么小就知道参加革命。好啊!”他显然很喜爱我们,揽着我们的肩膀,把我们抱得更紧了,我的脑袋偎在他那宽阔的胸膛上,手搁在他的肚子上——好软呐!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一边看一边不时的附在我们的耳边,给我们讲哪个是戈尔罗夫,哪个是欧格涅夫,哪个是客里空。他那浓重的南方口音,和他讲出来的那复杂的情节,我听不太懂,可我觉得他的话和他的胸膛一样,软和和的、热乎乎的。他和我一样看得挺开心,当看到客里空写了一篇假报道:“老将军的眼里没有眼泪,没有。”这时候,他竟然趴在我的头上放声大笑了。
第二天,在同一个土台子上,这位魁梧的军人同志被警卫员搀扶着,走上了讲台,对着我们上万军人作报告。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身体不大好。我问赵干事他是谁,赵干事告诉我,他就是我们山东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尊敬的罗荣桓同志。
后来,我50年代初来到北京工作,罗荣桓同志已经是总政治部主任了。1961年,为了《星火燎原》纪录片的解说词,我带着影片去送给他审查,罗荣桓元帅热情地问起我是哪个部队的。我就给他讲了当年的这段往事。我说我15岁的时候,你在莒南抱着我看殊科的《前线》呢!罗帅开朗地笑了。那一刻,我再一次感到,我走进革命的摇篮和人民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