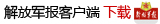王愿坚在写作中
三
房东老大爷给予我的温暖,是我人生的第一课。然而,这一课远远没有上完。我入滨海中学学习一个多月之后,1944年的9月,日寇对滨海地区的万人大扫荡开始了。侵略者的铁骑从不同的方向向西进攻,朝莒南的中心区包围,整个根据地军民投入了残酷反扫荡的斗争。我们滨海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也投入了这场战斗。
令人羡慕的是那些大同学们,他们身强力壮,领到步枪和手榴弹,随区中队和县大队参加战斗。我们这些年小的男孩子和一些女同学,被留了下来。
记得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们在十学路的大街上集中。天下着毛毛细雨。部队集合起来,我们滨海中学教导主任周抗,是一位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他严肃地走到了队伍的面前,完全不像前几天教我们唱“什么花开放向太阳”那么和颜悦色。脸色阴沉,略略有些歪的嘴歪得更厉害了。他肩上扛着一支步枪,大步走到我们面前,什么招呼也没有打,就厉声说道:“你们,真到了战斗的时候,都变成了革命的盲肠!”
我学过生理卫生课,知道盲肠是人身上最没有用处的一个器官,如今我们被说成了盲肠,心里肯定有点不愉快。“是盲肠!”周抗主任提高了声音说。“现在,需要拿起枪来,你们拉不开枪栓,需要拔出手榴弹去,你们连20米都投不了,炸不着敌人,还伤了自己。怎么办。只好把你们打埋伏。”
打埋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名词。经他的解释,我明白了,是把我们分别地送到老乡家隐蔽起来。周主任具体交代我们:“你们男孩子去给老乡当儿子,女同志把头发改造一下,握成一个小纂,去给老乡当儿媳妇。”队伍里传来了女同学的笑声,周主任却没笑:“有什么好笑的,就是当媳妇!不过,你们的丈夫在哪里,只有天晓得了。这样安全,这样可以躲过敌人的视线,可以保存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就分别去当儿子、当媳妇去吧!”
接着周抗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本来你们参加革命,就是给人民当儿子,当女儿的,就是人民的儿女。现在,无非是让你们去开始学着做一个人民的好儿女,去吧!”接着一批农村干部走过来,你领两三个,我领四五个,我们一个中学的男孩和女同志,就这样被瓜分了。
我被分到了张家连子坡张大娘家里,张大爷去支援前线了。
张大娘热情地收下我,把我身上用泥灰涂黑,然后让我穿上了不知哪里弄来的一套男孩的衣服。于是我就成了张大娘的“儿子”,大娘自己还有一个小女儿,不满两岁,是我的“妹妹”。张大娘给我第一个训练,就是说:“王同志,以后我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蛋蛋。”我说好,大娘笑了。说:“叫一声娘。”我就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娘。这一声娘叫出声之后,我觉得和张大娘亲近了很多。但是我真正把这个娘字从心底里叫出来,那是10多天以后了。
那天,突然发现敌情,张家连子坡的老乡们,拖大带小,钻进了一条山沟逃难。张大娘抱着小女儿,手里拿个包袱,然后把一个小牛犊子的缰绳递到我手里说:“跟我走。”于是,我们就汇入逃难老乡的人流之中。
9月末,穿一身单褂,冷风料峭,大娘就把我揽在怀里,用她的体温暖和着我。这样熬过了一天,直到太阳落山,解除警报,我们才回到了家里。
到家一看,院子里大椿树下,到处是马屎马尿,满地是喂洋马吃剩的一些散落的高粱。原来,大娘家里唯一剩下的一点粮食,都被日本鬼子喂马了。我们进了门,大娘什么也没有管,解开放干粮的那个篮子(莒南话叫浅子),把上面的包袱绳解开,里面是两个地瓜面做的窝窝头,大娘抓起来,都递给了我,然后,自己抱着小女儿,到里屋去了。
饿了一天,我也实在顾不上别的了,三口两口就把两个窝窝头吞下了肚子。当我吃完的时候,忽然发现,“妹妹”在里屋哭得那么厉害,嗓子都哭哑了。我心想,会不会是着了凉,生病了,赶快撩起门帘看一看。只见大娘坐在坑沿上,把孩子揽在怀里,顺手从身边柳条筐子里边抓着花生壳,放在自己嘴里,慢慢地嚼烂,又吐出来,用指头抹到了小妹妹的嘴里。我知道,这些花生壳是留着当柴烧和用来喂猪的,又苦又涩又硬,难以下咽,“妹妹”当然吃着不舒服,也就不肯吃,就哭闹起来。她还不到两岁呀!
我明白了,家里就剩下了两个窝窝头,大娘给我吃了,让自己亲生女儿吃这嚼烂了的花生壳。就在这一霎时间,我发现她就是我娘,我真正的亲娘,比亲娘还亲。我喊了一声“娘”,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哭了起来。
大娘抚摸着我的头,说别哭了,别哭了。我埋怨地说:“娘,你说一声,我给妹妹留一点嘛!”娘半天没有吭声。半晌,她摸我的头说:“小王啊,你是革命干部,你正在学习,你学好了能打日本鬼子。只要打走了日本鬼子,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
什么叫做人民的爱,什么叫做人民是我们的亲爹娘,什么叫做人民子弟兵,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在这一刻,我懂了。
留在心头的这种感受,永远不会淡忘。10年以后,在北京一座楼房里,在一盏台灯的下面,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党费》,当我写到那个女共产党员,为了给组织交党费,不交钱,而交点实用的东西,腌了一些咸菜,交给红军游击队。当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久不见盐,想抓一根咸豆角吃的时候,妈妈又从孩子手里夺过来,放进了菜篮子。这个细节,很自然跳到了我的脑子里,来到我的面前,成为稿纸上的故事。它从哪里来,它就是张家连子坡那位亲娘嚼花生壳的形象,在我的作品里变成的文学细节。甚至于连对话,我都原封不动保留了:“同志,只要革命能够成功,不知能保住多少孩子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