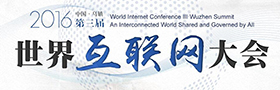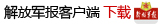方志敏
方志敏戴着镣铐写出了《可爱的中国》。直到今天,女儿方梅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父亲遗作时的那种激动。
第一次读到父亲在狱中写成的《可爱的中国》的那一年,方梅年方十七。如今,84岁高龄的方梅老人,还依稀记得当时那份激动:“爸爸,那是我爸爸写的。”
虽然,儿时的方梅记忆中并没有父亲的影子,但她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奶奶曾经告诉她,父亲长得清秀英俊,小时候被村里的人叫做“正宫娘娘”。养父母也曾告诉她,他的父亲善于演讲,他一讲话,大家围过来听上半天也不嫌累。在乡亲们的传言中,父亲的形象更是高大:骑白马、挎双枪,威风凛凛,来去无踪……
很长一段时间,在各种说法中拼凑起父亲形象的方梅,根本不相信父亲不在世了;赣东北的老百姓也不相信,方志敏已经牺牲——虽然关于“方志敏下场”的告示就挂在各村村口。乡亲宁愿相信,那是国民党造的谣。
天天盼着那个英俊的父亲回到自己身边的方梅,出生在国民党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的1932年冬天。那一次“围剿”,国民党出动近40万兵力,蒋介石亲自担任“剿匪”总司令。
炮火就在不远处爆炸,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缪敏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然后把这个哭声像小猫一样的女孩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夫妻俩最后一次去老乡家看望女儿时,缪敏担心这孩子太弱养不活,方志敏却说:“严冬的梅花,生命力最强!”
战火岁月中出生的5个孩子分别寄养在各处。方志敏为他们取名松、柏、竹、梅、兰。方梅长大后才知道,那是父亲最爱的一副对联: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刚刚出发,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告别妻儿,也告别他亲手创建的闽浙赣苏区,率红10军团踏上了孤军北上之路。
虽然是同样的“北上”,走的却是不同的路线。
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主力红军面临的是一次向死而生的远征,那么,担负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任务的红10军团,却几乎是一支把活路堵死的死亡军团!
在20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部队屡屡受创。1935年1月,红10军团退至赣东北边缘,决定进入苏区休整,不料敌人早已设置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线。
一番浴血征战之后,原本,方志敏和军团参谋长粟裕带领800多人率先冲出了封锁线,但大部队还陷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在方志敏召集的最后一次军政会议上,他坚定地说,我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不能先走。遂调转马头、复入重围。
多年以后,粟裕将军还记得方志敏当时的决绝态度:明知凶多吉少,依然毅然决然。
回到苏区的几百残兵在粟裕率领下突出重围,后来发展为中国工农革命挺进师,而与2000将士苦守怀玉山的方志敏,却在漫天的大雪中不幸被俘。
最先发现方志敏的两个国民党士兵本以为会发大财。谁知,在方志敏身上,他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搜到,“怎么会呢,这么大的官,会没有钱?”“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方志敏怒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美联社记者这样记录国民党“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的场景:“带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使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
在狱中,方志敏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战斗。他争取到了同情革命的胡逸民、高易鹏等人以及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前者辗转4次从狱中送出了方志敏的手稿,而后者则把方志敏脚上的镣铐从10斤的换成了3斤半的。
正是这副镣铐,在20年后成了当地政府最终找到烈士遗骸的重要线索。
1955年,在方志敏就义处——江西南昌下沙窝,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副棺木、很多骨头和一副镣铐。经凌凤梧等人辨认,镣铐和棺木正是方志敏受到的特殊“待遇”。血样对比之后,9块遗骨被认定为方志敏的遗骸。
又过了22年,方志敏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方梅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先是细雨濛濛,尔后碧空如洗,当灵车经过市区时,街道两边站满了含泪送行的老百姓……”
母亲缪敏没能等到送别爸爸的这一天。就在父亲遗骸安葬仪式的一个月前,曾经与父亲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母亲,匆匆辞世。
方梅说,小父亲10岁的母亲名字里的“敏”字,也是父亲送她的订婚信物。成婚那天,父亲曾给母亲取了一个化名,叫“李详贞”,与父亲直到被捕时还在使用的化名“李详松”,又是天成的一对。
方志敏被捕后不久,缪敏也落入敌手,被囚禁于与丈夫关押地只有一墙之隔的南昌女子监狱。当方志敏望着报纸上妻子被捕的照片难过时,劝降者不失时机地提出,以跟缪敏见面作为“发表一个倾向声明”的交换条件。
方志敏当然说不。后来,他曾流着泪对凌凤梧说,缪敏是巾帼英雄。两年后,缪敏被党组织保释出狱。夫妻俩曾经近在咫尺的相隔,终成生与死的距离。

方志敏被俘后大义凛然英勇不屈。
母亲渐渐年长,一天天长大的方梅也从母亲身上深深感受到了这对红色夫妻间那种刻骨的思念。方梅回忆,性格刚强、“一不对就会掏枪出来”的母亲,一提到父亲就会泪流不止。结婚时父亲送母亲的“英雄”牌钢笔,母亲一直用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一直用到了笔头磨得溜光。
母亲把对父亲的思念,写成了《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红色风暴》,还在51岁那一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而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后来在颠沛流离中遗失的那封信,母亲在后半生还一直在寻找。
方梅与母亲直到全国解放那一年才得以相见。与被母亲带到延安、后来上大学并留学苏联的两个哥哥方明和方英相比,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方梅吃了太多的苦,母亲想要弥补这份遗憾。
母女俩几乎同样的倔强。母亲不得不把女儿锁在屋里,逼着她读书学习。就在这时,方梅第一次读到了父亲的遗作《可爱的中国》。
“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一遍遍朗诵着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刚刚识字不久的方梅欢呼起来:从此我可以讲我的家史了,从此我懂得“祖国”是什么意思了——祖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的母亲!
从被俘到就义的日子里,狱中的方志敏戴着镣铐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记实》等30多万字的文稿。才情、激情、真情,这囚禁中的文字,成了影响几代人的经典。
同样从农村走来的毛泽东,欣赏方志敏靠“两条半枪”打出了两个红10军的才干,他称赞在敌人重重“围剿”中屹立不倒的闽浙赣苏区为“方志敏式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和农民问题上,两人更是早有共识。
蒋介石同样看重方志敏。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时,蒋介石多次设宴款待已经成名的方志敏。方志敏被俘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还许以江西省主席之职,但得到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赶紧下命令执行吧。”
既然一代英才不能为己所用,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
1935年8月6日,距37岁生日仅半月。被押解至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上默默站了几分钟,然后猛地一转身,说:“来吧!”
大雨之前的风,吹动着方志敏的长发。枪声响起的那个日子,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正迎着狂风暴雨,在川西茫茫水草地上艰难跋涉。
方梅后来常常问自己:父亲最后想了些什么呢?
已经八十又四的方梅说:“那几分钟里的思绪,父亲想的肯定是他梦中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