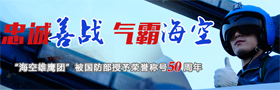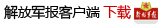进墨脱“孤岛”体验奉献
■郑蜀炎
直到1990年,成都军区驻西藏墨脱某部,在军事记者的脚下还是一个空白,没有记者徒步进入过墨脱。那年7月,我和周宗奎、徐文良两位军报同事,踏上徒步进墨脱之路,决心把驻墨脱官兵的事迹报道出来。
墨脱是当时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进入墨脱的大门,是海拔5000多米的多雄拉山。每年7至10月间,最低海拔4700米处的山垭口会化开一条“门缝”,驻墨脱某部今后一年的给养物资,以及去年积压的信件报刊,都将利用这3个月时间背进去。
那天一大早,我们打紧绑腿,穿上用塑料薄膜做成的简易雨衣、戴上草帽启程了。
要闯的第一道关,是必须在上午翻越多雄拉山。上山时我们气喘如牛、汗流似雨,因闷热难耐,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而两脚却每一步都踩在厚厚的雪里。下山时坡度极陡,在4000米的雪线上,我们为了节省力气,就坐在雪地上朝下滑;下了雪线,脚下全是冰雪化出的飞瀑,急流凌空扑下,部队同志提醒我们,不能互相搀扶,不然容易一起冲下山沟。我们只能死死拄着树枝削成的手杖,虽然被雪水浇了个透湿,但紧张得竟然没有感觉到冷。
闯过6座冰川,蹚过8道湍流,便进入到世界第二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踏上墨脱路。这是一条长约120至150公里的山道,是经人脚兽蹄踩踏、从树根岩石间磨出来的,一般要走3到4天。当我们了解到墨脱官兵一般是两天走完后,决定也走两天。道理很简单,和墨脱官兵用同样的时间行进,才能更真切了解这段路程的实情。说是走路,其实是在乱石、树根和雪水间连续跳跃着前进。深处可没膝,浅处则长满青苔,一不小心就是一个跟头。开始谁摔跤还相互笑话一下,可很快就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只知道机械地迈出已被冰水泡白的双腿,近乎绝望地盼望着当晚的宿营地。
天完全黑下来,在强行军14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食宿站,烧了锅稀饭用压缩干粮把肚子填饱,然后蜷伏在满是跳蚤的床上睡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遇到的第一个险关是“老虎嘴”——这条从山崖绝壁间炸出来的路仅一米宽,而且四周没有任何可以攀抓的树木,下面是数百米深的深渊。我们“蜘蛛人”般贴着山壁,用手死抠着石缝,一步一挪地越过了这段5公里长的险关。过了“老虎嘴”,又进蚂蟥区。我们走一段就停下来搜索一番,每个人身上都拔出来几十条蚂蟥。
又经过13小时的跋涉,“墨脱路”终于有了尽头,部队营房已经遥遥在望,可我的腿一步也迈不动了。好在部队发现了我们一行,派出十几个战士把我们架了回去。一夜之后,腿肿了起来,连上厕所也无法蹲下。接着,大脚指甲盖整个脱落了……
在连队拄着手杖进行了几天的采访后,我们又按原路走了一遭。记得在最后通过多雄拉山垭口时,由于体力实在不支,我们扔掉了除照相机和采访本外的全部物品,完成了墨脱路上的最后冲刺。
墨脱之行,我们采写的《铁肩担国防》获“第二届全国现场短新闻”一等奖,长篇通讯《墨脱军人竞风流》在军报上大篇幅刊登后,西藏军区派出送报组背着报纸进墨脱,给墨脱官兵每人两份报纸,一份寄给家里亲人,一份自己保留。两年之后,中央军委授予该部“墨脱戍边模范营”荣誉称号。
毫无疑问,这是对记者最高的奖赏。我也在采访日记里写下:凡有中国军人的地方,就应该有解放军报记者的足迹。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部原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