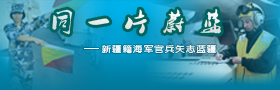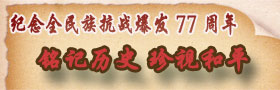建设性地践行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重大的体制机制变化带来的是非常深刻的国家安全行为变化。在总目标没变的情况下,手段会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推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机制的建设,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对外战略及其行为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对外战略变化的转折点是2013年11月26日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2014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解释了何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其中,他提到了“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这句话的指向非常清楚。从这个具体的指向可以看出,我们的外交思路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更加强调结果,而不是强调状态。以前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首先强调状态,就是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知道,稳定一定不是常态,它只是个临时状态。那么,我们对稳定的要求也存在相对稳定性。而现在,我们更注重在运动中保持运动方向的明确,至于是不是稳定的,已不是重点。
但是,还是要强调一点,我们的基本战略没有变,只是基本战略的执行手段在发生变化。
首先,我们继续保持了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这是党的十八大和全国“两会”后,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这是我们的传统,但也有突破传统的地方。例如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实现了庄园会晤,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不再追求形式,而重在内容。当然,奥巴马的想法有所不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其次,中国更加重视远端外交。比如说我们对非洲、拉美,包括“金砖”国家的顶层外交等。我们的视线开始从大国转向世界。以前,中国的外交一度就是非常重视大国,甚至有人认为搞定了美国,外交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是个大国,我们要向远端扩展,不能再从美国的视角看问题,否则永远走不出去。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不再是大国能主宰的世界了。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关系基本上就是大国关系,小国是被动的。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让大国头疼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基本上不是由另外一个大国直接造成的,而是由某些小国造成的,小国折腾大国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大概算得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表现了吧。
第三,强调周边国家的主体性。我们承认周边国家有自己的主体性,不再仅仅从大国视角,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视角去看待周边。这一点是与我们全球视野的加强并行不悖的。
第四,从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实施了重大的战术调整,开始引入“负面清单”。什么是“负面清单”呢?以前,中国外交是谁惹事就优先处理和谁的关系。比如说,菲律宾捣乱,我们就邀请它的总统来华,给他做工作。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做日本的工作,争取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做出让步。其实这不叫“负面清单”,这是“负面优先清单”。而从2013年开始,中国外交的“负面清单”效应日益凸显。2013年的前10个月里,中国与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要么在中国国内,要么在国外都见过面,只有两个国家例外,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
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回归了常识。什么是常识?常识是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而过去,我们曾是你越不跟我好,我越要跟你好,和你玩。以后没这个事了。老实说,把菲律宾列入“负面清单”有点高看它,因为它在不在“负面清单”里根本不重要。但日本则不同。
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承认,在今天东北亚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关系问题,而它的表象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与日本,我们当下的策略是跟你“耗”到底,看谁能熬过谁,我也不打你,打的话,性质就变了,但我也不跟你修补关系。展望一下未来几年,中国在周边地区最基本的外交问题就是如何打破日美同盟。打破日美同盟是一个要求有技术和有决心的活动。不能让日美同盟进一步紧密化。比如说,中国武力攻击钓鱼岛,这样的结果不是打破了日美同盟,而是巩固了日美同盟。但如果中国忍了,也是在巩固日美同盟,因为日本就成为美国非常有用的帮手,美国就会更加重视日本,使得日本在这个地方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导致中国面对着更大的日美同盟压力。
中国对日本的最优策略是增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给美国造成的成本。中国已经用这个方式处理一个对手了,就是菲律宾。日本不是菲律宾,日本的能力很强。那么中国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不能指望让美国人觉得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不重要,但是可以想办法让美国人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烦人的国家。我们要击破日美同盟,既不要把它挤到一块去,又不要让它轻易获胜,跟它熬着,这是最好的方式。使得日本想成为美国的“本地代理”却不能。
具体怎么办?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一个底线,这是不能启动日美同盟使用武力的一个条件,即中国不直接武力占岛。那么美国就不会去较真,客观地说,美国从心理上并不想出兵,所以只要不给它这个理由,不让它无路可退,它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不出兵的。但在除此以外的任何一个国际场合,中国都要打压日本,不让日本成为亚洲政治大国。这样,才会使美国对日美同盟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目前,我们在亚洲要建立的区域秩序,和日本的国家意志、美国的国家意志是冲突的,最后只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第五,除了上述的一些对抗性的举措,我们也做了一些建设性工作。在周边建立一些小区域、多边的合作机制,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等。
从地图上看,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周边划了很多小圆。“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然后从印度洋穿过去,一直到欧洲。“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陆地上从中亚过去,也到欧洲方向。这两条路线就把中国的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涵盖进去了。中国和南亚存在一个缺口,所以我们推动建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西南方向解决出海口的问题。“中巴经济走廊”是特殊的,因为中巴关系很特殊。所谓区域合作,就是不追求一个全球性的框架,而试图建立小多边的地区框架,用地区架构解决地区问题。
为什么要搞“小多边”?例如,“海上丝绸之路”不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能参加,有些国家是不能参加的,比如说菲律宾。我们在每一个区域范围内,选择一批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建立差异性的示范。这个逻辑是美国的TPP的逻辑,谁对我好,我和谁玩,互相受益。
以上这些战术修订纠正了以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乱。以往我们的目标是自身发展,保持周边的稳定是手段,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把保持稳定变成了目的,甚至为此牺牲发展。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战略思路不清楚。
过去的线路是先谈稳定,最后谈主权,那其实什么都谈不成。现在,我们的表述非常清楚,从主权到安全,最后到稳定。我们在外交战略上不是变更了战略,而是作了一些次序上优先顺序的调整。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变化,从回避矛盾到险中求进。我们以往是息事宁人的态度,现在的策略中,险中求进是最为明显的。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变化很清楚。最核心的表象是我们海上维权实践在行动指南上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总体来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没有大的改变,我们要对战术和策略层面进行修订,关键是要精细化我们的方式方法。一方面,专业部门要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另一方面,公众对这些问题要有更多的容忍和耐心,这是一个要试错、累积经验的过程。
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内外兼备。在国内,我们现在最突出的安全问题就是反恐问题,昆明“3·01”暴恐事件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告诉我们,国内的维稳问题不是一个省份的局部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维稳问题。
此外,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还必须审慎对待信息安全问题。无论是昆明“3·01”暴恐事件,还是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都暴露出我们现在在互联网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互联网管理水平必须加强。信息安全问题难度非常大,因为传统战略问题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反恐问题有其他经验可以汲取,信息安全问题在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难题。美国也有自己的软肋,斯诺登叛逃之前,美国在跟中国谈互联网行为规则,中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斯诺登事件”后就什么也不用谈了。中国认为,首先互联网自由是相对的,这个自由是包括了信息自由以及系统自由。第一,我们认为美国人说互联网无中心是胡说,互联网中心在美国,我们的安全是受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加强自身安全防范能力;第二,我们认为,除了信息的流动需要受到保护之外,信息本身应是无害信息,不能在互联网上散布仇恨、教授恐怖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大部分的信息来源已经不是来自电视、报纸,不是来自固定的互联网接入设备——电脑,而是手机,而手机上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是“自媒体”。这是传统媒体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从来没有遇到的新现象。这无疑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