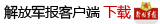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三个层面突破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时面临的普遍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但有两个规律性现象值得我们重视:一是越接近崛起目标,安全困境就愈加凸显,无一例外。二是历史上崛起国在遭到守成国打压时,多采取战争手段,但结果往往是守成国被削弱,崛起国遭遇夭折,另一个相对超脱的大国走上历史舞台,即真正崛起为新的强国的国家都是所谓“第三者”,或者说“渔人得利”。
如从17 世纪上半叶到18 世纪初,法国一直是欧洲多次战争中的主角,它先后同传统强国西班牙、荷兰及欧洲多数大国直接交战,但结果却是英国成为了最大得益者,并一跃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气势汹汹的德国向国际秩序发起挑战,最终却是迟迟参战的美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并在二战后成为新的世界霸主。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战略学界就开始探讨解决安全困境的路径和办法。很多学者认为:安全困境的根源是互不信任。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会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所以要做到国家之间的完全信任几乎不可能,这是由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决定的。安全困境虽不可根除, 却可以缓解,而缓解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建立某种机制(包括国际法律、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来加强相互信任,减少猜疑和误判。
历史上大国崛起主要有两种战略选择:“搭车”(即搭霸权国的便车) 与战争,并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中国的大战略是和平发展、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不能将其理解成宣传口号,也不能看作权宜之计。这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梦之所系。习主席反复强调,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就是要竭力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战争覆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具体战略和策略上努力缓解安全困境,想方设法突破这一瓶颈。
从大的方面看,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战略,就是与守成大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另一种就是间接战略,即通过迂回的方式,既合作又斗争,实现大国崛起。显然我们应该采取第二种战略即间接战略。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不仅是接触合作加防范遏制,更多的是采取规制的办法来约束中国,并做好了规制失败的准备。美国的规制也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开辟了中美斗争的新领域, 即给我国提供了在融入现有体系时改造机制、改变规则的机遇。我们应通过长期努力,争取创建新机制,制定新规则。在这个过程中,要时刻做好危机管控,处理好与美可能发生的各种摩擦和冲突,避免小危机升级为大危机,小冲突演变为大战争。
所以,不能将今天的中美斗争仅仅理解为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它具有更加广泛的含义,包括围绕机制建立和规则制定的斗争,这将为中国和平崛起赢得时间。
因此,在突破安全困境的路径上,应从三个层面入手。
一是与美国关系层面,通过与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等利益关系, 达成真正牵制美国的目的。在利益捆绑中,逐步实现美对中依赖大于中对美依赖,使美国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损害达到其难以承受的程度,就有可能避免两国最终摊牌,我国面临的安全困境也将得以突破。
二是在国际层面,实行加强合作与坚定维护主权并行的政策,做到两手抓、两手硬。2014 年,我国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做了许多新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提出“一带一路” 战略,主办APEC 会议,设立金砖国家基金、丝路基金,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等。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在2014 年7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达成的协议,也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创设的银行,意味着经济总量占到全球21%、拥有全世界40% 外汇储备的金砖国家,在全球金融架构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还应给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不仅是经济金融和贸易产品,也应考虑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以此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
三是在国内层面,做大做强军事实力,这是最终突破困境的唯一途径。表面上看,新兴国家军事实力的增强是引发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但实质上,新兴大国军事实力与守成大国存在一定差距才是崛起国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加快发展,实现强军目标。当新兴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真正达到让守成大国不敢妄动时,安全困境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战略决心、战略意志、战略勇气、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力。
缓解和突破安全困境,要以习主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这是我们今天思考如何突破安全困境的根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要求我们用总体的而不是单一的、辩证的而不是孤立的、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观点来看待安全问题,筹划安全战略。筹划和实施安全战略,不是简单地将各种安全举措相加,而是将各种举措相乘,做乘法;也不是将各个安全部门的职能简单地综合,而应该将过去各个安全部门的职能收指成拳,形成合力。在此基础上,逐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突破安全困境,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
(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孟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