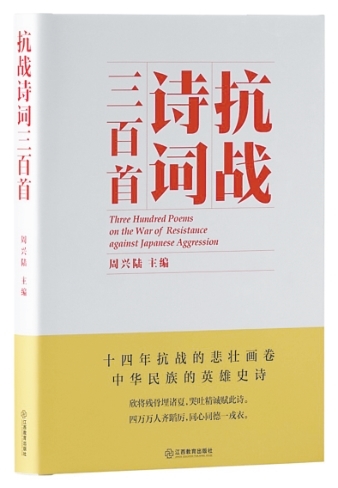
▲《抗战诗词三百首》,周兴陆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家国情怀与文脉赓续
■张子阳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名言,在十四年抗战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与升华。战争年代,国家命运与个体精神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周兴陆教授主编《抗战诗词三百首》所记载的,正是在关乎存亡的历史现场,于烽火中淬炼而成的一首首动人篇章,是这段历史最真切、最鲜活的记忆与见证。这些作品或慷慨激昂,或沉郁悲怆,或坚定从容,记录了社会各界人士于国难之时发出的呐喊,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与史料价值,亦为身处当代的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战时期的社会氛围,理解何为中华民族之真精神,中华文化之真境界,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纵观《抗战诗词三百首》所选诗篇,昂扬进取,奋发有为的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是其主旋律与重要内容,尤其是身处前线的将领与革命领袖所作诗词,书写着民族气节与个人信念的交响,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例如朱德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指挥时所作《太行春感》:“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气象雄浑、格调高昂,以“忠肝”“壮志”彰显报国之心,以“百战新师”“三年苦斗”写照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更以“驱逐倭儿共一樽”收束,传递出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可谓一代人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宣言;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远赴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时,于异国他乡写下《旅居美国旧金山杂诗》,诗中“乘风破浪非虚语,万丈浮云在下头”之句,以传统意象寓个人豪情,抒发胸怀天下、不畏艰难的恢宏气魄。正是这些诗词,让我们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非虚言,无数个体的努力聚沙成塔,汇流为江,凝聚成了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国人渡过难关,迎来最终的胜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个体精神的星火,终须凝结为集体主义的力量,才能形成震撼人心的燎原之势。《诗经·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集体主义精神,于数千年后的抗战诗词里激荡出了最强的共鸣音。在《抗战诗词三百首》中,“四万万”“四兆”等字眼被反复提及,它们不仅是人口统计的冰冷数字,更是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承载着炽热的民族自豪感与共同的责任意识。著名法学家黄右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难以抑制悲愤之情,挥笔写下“四万万人心不死,枕戈待旦具同情”(《农历中秋愤东北之变夜不能寐二首》其二),道出广大民众绝不屈服,誓要同呼吸共命运的抗战心声;郭沫若于1937年回国抗战前夕,作《归国杂吟》组诗以明志,组诗其二曰“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将个人的报复志向融入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潮,与家国同频共振;梁寒操《“一·二八”六周年放歌》,痛悼战争中的牺牲者同时,高唱“我有同胞四百兆,人人争把摩拳擦。拼将流血成大河,国耻明朝全洗刷”,以集体主义之精神激励自己,以及身处战火中的同胞。除此之外,众多抗战诗词也以赞颂保家卫国置生死于度外的前线将士为主题,例如淞沪会战中誓死保卫上海的“八百壮士”,即有胡朴安《八百壮士歌》、胡怀琛《八百孤军》、冯玉祥《八百好同胞》等加以描绘,因而被更多人熟知,深入人心。集体主义精神塑造了抗战诗词的最鲜亮底色,而抗战诗词又在广泛传播之中,不断巩固和升华人们的集体精神,传达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决心。
另一方面,本书所收部分旧体诗词,在传统诗词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革新,例如易君左《鲁南大捷歌》、黎锦熙《铁军抗战歌》等,篇幅宏大、语言明快、节奏铿锵、情感充沛,既延续歌行体之传统,又有口语化的民间风格,一时广为流传。抗战时期的诗词创作,不仅使得式微已久的旧体诗词重焕生机,更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新变,展现出中华文脉危难中的顽强生命力。“国家不幸诗家幸”,《抗战诗词三百首》为我们展现了战争时期文化界齐心协力,共同抗敌的庞大图景之一角,其中蕴含着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时人为赓续文脉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昭示着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当重读这些作品时,我们不仅是在回望一段血泪铸成的历史,一段不容忘却的苦难岁月,更得以在文本的深处,审视中华民族于非常时期展露出的强劲的精神韧性。这种精神基因已深深镌刻于历史的进程中,成为抗战史乃至中华文明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永远被后世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