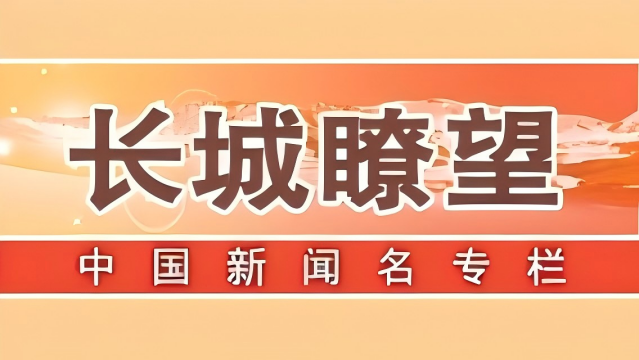论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
■丁晓原
报告文学因其独有的文体魅力,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呈现出多彩斑斓的景观。其中,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每每让人眼前一亮。进入新时代以来,强军实践为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有的军事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也存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认识不清、对创作规律把握不准、作品文学特质相对偏弱等问题。本文从报告文学本体认识出发,阐述报告文学创作规律,以期对读者有所启示。
80多年前,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谈到:“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由此,我们习惯上把记录时代、存活历史的报告文学,指称为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成为独具活跃度的重要文体。文随时移,固本开新。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报告文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它的文体建设。
一
报告文学是“事实文学”。所谓“报告”,就是事实的报告。事实客观存在:语言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自然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本真呈现。但是,报告文学的“事实第一性”,要求作者的写作应该厚道诚实,最大程度上逼近事实本身。有一种说法较为流行:报告文学写作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一种较为暧昧的表述。首先,“大”“小”之间很难厘定把握。再者,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叙事文学可以借鉴小说的叙事艺术,但大段连篇地记写带着引号的过往人物的对话、无根漫溢的情景再现等写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倡导报告文学的写作应坚持大事务实、小事求真的原则。所谓“大事务实”就是关系写作对象根本规定性(定时、定点、定量、定性)的事实须得核实,务求精准;所谓“小事求真”,就是一些必要场景的想象性再现(“修复”),要符合人物、事件和场景等的真实性逻辑,不可想当然地任意书写。这些书写须把握分寸,获得自洽的逻辑。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事实是要件,但成为要件的事实必须具有书写价值。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生成,以题材的价值含量为前提。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写作的题材决定论,而是表示这类非虚构写作题材须具有某种意义的前置性。有价值的报告文学写作题材,是具有时代价值、历史意义和人文风景的新质题材。作品要为读者提供新的事实、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应当对时代有着敏锐的观察、对历史有深入的勘探,从中发现、选择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人文价值的初始性、独特性题材,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加以展陈。近期出版的《龙腾伶仃洋——深中通道建设纪实》(李春雷)《为珠峰测高的人们》(钟法权)《创作之伞——中国文字著作权保护纪事》(李燕燕、张洪波)《巴黎有片榕树林——海外温州人的家国情怀》(朱晓军)等,就以题材的取新别异,奠定了作品的价值,为读者所关注。
有一种倾向值得写作者重视:在一些主题写作中,题材选取、视角选择等显现出同质化、雷同化的现象。作家需要正确理解把握主题创作的要义。主题创作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点和热点,是来自时代生活的召唤,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使命之所在。有价值的主题报告文学,是以独特性、典型性的题材及其具体内容表现时代重大主题的。主题创作具有广泛丰富的题材空间。同样是反映建党历史和精神的作品,徐锦庚的《望道》、丁晓平的《红船启航》和徐剑的《天晓:1921》,作者取材视角不同,表达的主旨各有侧重,写法也各显其长。
报告文学作为以事实为基础的文学,需要提供丰富饱满、有表现力的事实。这样的事实,自然无法在书斋中闭门造车,它需要经由作者深入的采访、扎实的田野调查、必要的相关知识的学习储备等,才能积累获得。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灵敏度高的显示器,可以清晰地照见作者劳动的量与质。读者阅读报告文学,期待读而有得、得而受益。但有一些作者给读者提供的信息“注水”太多,作品的信息(事实)载量不足。空洞无物的报告文学缺少非虚构的力量,自然也无法召唤起读者的阅读热情。
二
所谓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质的属性,是文学的规定性。何谓文学?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们既需要提取文学性的“公约数”,又要看到不同写作样式文学性的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作为“公约”的文学性,它诉诸接受者对形象、具体、感情等的感知;强调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作者应具有及物达意、文约意丰的语言能力。报告文学应当满足这样一些“公约”的要求。但报告文学又是基于事实的文学,它不可虚构,不能恣意想象,其文学性生成有着自在的独特性。
文学来源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来源于生活。生活是没有彩排的舞台,其中的不确定性演绎出的种种出人意料又客观自在的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等,其文学效果绝不亚于通常的虚构想象所得。在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中,题材事实与文学性之间具有直接关联。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文学性元素构成了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基础。在报告文学中,报告不只是报告,也是文学的前提。正因为这样,富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更舍得在题材事实的深度获取上花更多、更切实的功夫。徐剑的《西藏妈妈》是这位“老西藏”新行走之作。作家在艰难而遥远的行走中,采访了百余位在福利院照护孤儿的“妈妈”。作品中重点人物的故事,闪耀着时代性与母性、人文关怀的光芒。杰出科学家袁隆平的人物传记有近百种,陈启文的《袁隆平全传》,其“全”,是因为作者通过精心独特的采访,对传主有更新更全面的发现和了解。作者走进了袁隆平更丰富的世界:人生的世界、科技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尤其是在人物真切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透视中,让作品具有了充沛的文学性。
报告文学虽为非虚构写作方式,但并不意味着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放弃作者的主体性。没有主体性就没有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既内置于书写的对象之中,同时在文本建构中又需要作者对提取到的事实材料作审美性的呈现。这种呈现基于叙事的设计,对材料进行具有审美表现力的调度。所谓调度就是将原生的、散在的材料,作有序列的情节性、场景式的细化,并根据叙事的需要进行结构性重置。这种调度和重置,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方式。比如,何建明的《山神》,主人公是“时代楷模”黄大发。作品开篇叙写行走高山“天渠”的艰危,以此蓄势强化叙事的悬念。
三
无结构便无文学。结构既包括具体的起承转合叙事结构(时间与空间),更指总体性的规划布局的表意结构(思想与艺术)。兼顾这些要素并能使其有机优化组合,并非易事。结构意识淡薄,叙事“无为而治”,这是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长篇写作者重视的问题。
报告文学的结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模式化是其重要“病症”。这显然与作品的结构建制和叙事调性的不当设置有关。报告文学写作题材丰富多样,书写的空间也很广阔,写作者本身也各有不同的情况。文学创作是一种求取独创性的精神活动。报告文学写作的“去模式化”,需要更加注重叙事的对象化建构和作者的主体性,有效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所谓叙事的对象化建构,就是能从书写的题材内容中,寻找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结构肌理,从中获得契合此一题材的及物达意的叙事结构和表意结构。所谓作者的主体性,更强调作者的创作优势与题材类型的适配,扬长避短,写作适合自己的题材。
题材类型和主题取向不同,相应地,作品叙事的组织方式也需调适。何建明的《浦东史诗》从家族史和个人经验切入文本,关联起宏大与微观的联系。作品对于“上海”一词的全新解读,既体现作者的主体性风格,又彰显出浦东开发开放所蕴含的时代精神。纪红建的《彩瓷帆影》,以长沙铜官窑题材书写“一带一路”主题。作者从一艘唐代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发现切入叙事,构建了千年前彩瓷制造、商贸的历史叙事和作者寻找“彩瓷帆影”的当代叙事。两种叙事交融错落,具有很强的阅读牵引力。徐剑、李玉梅的《强国记——中国知识产权的力量》,记述的是中国专利金奖项目成果和发明人的故事。作品整体上采用了科技叙事和文化阐释相结合的结构。文化阐释嵌入与黄河、湘江和珠江时空有关的主体叙事之中,试图解读中华江河文明与当代高新科技创造之间的逻辑密码。这种总体性结构,有效地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表达,也彰显了作者的个性风格。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