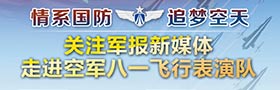引子:1965年,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钟有煌带领学员拉练到遵义,听说当地有一座受百姓香火供奉的无名“红军坟”,经多方考证,发现正是1935年长征到达遵义后失散被害的战友龙思泉。近几年,第三军医大学经过多方考证,围绕“红军坟”挖掘整理出一段“薪火相传红医情”的故事,特地采集了有关四位故事亲历者的讲述,拼接还原了这个红色纪实。
“干人”讲述:那支部队和那个小卫生员
讲述者为亲历者之子,73岁,他从已过世的母亲那里听来了这段故事。
80年前的那个冬天,可恶的“鸡窝寒”到底来了。村里的“干人”(贵州话,穷苦人)发烧、寒战、腹泻,却无医无药。“瘟病”夺去了一条又一条性命。
外头锣鼓“通”地响了一声:“嘿,各家各户注意了,上头说的,‘赤匪’就要来了,这几天注意关门息户哟!”听到乡丁吆喝,我心头一紧,于是一路小跑回家,赶紧把消息告诉病了多日的娘。
16岁的我轻轻扶着娘亲,透过门缝往外看:冬季清冷的夜色中,这支部队打着火把,穿得破破烂烂,但队伍整齐又安静,前头的人举着一面鲜红的旗帜。一路走来,没有嚎叫,没有抢劫,甚至,我看见一个当兵的往草棚里躺着“等死”的“干人”手里,塞进一小块干饼。很快,这支几百人的队伍集中到场坝里,由一条条直线化为几个规规矩矩的方块。
“再次重申,不准私拿群众财物,不准向受蒙蔽群众开枪,不准侮辱妇女,违者杀头!”站在队伍最前头的人在喊话。“稍息,立正,就地扎营!”
队伍解散了,那些兵解下背囊,直接铺开,睡在野地里。
一夜无事。早上,我轻手轻脚地推开门,探出头一看,那些兵已经忙碌起来,有的往泥坯墙上写着大字,有的拿着锅子和铁铲朝村外走去,有的给老乡起劲儿讲着什么,还有些兵帮着村里的老人家劈柴挑水。后来,我才知道,那用墨、炭灰和石灰块混合起来,刷在土坯墙上的大字是“打土豪分田地” “我们代表工农”。
“红军”不烧房子、不抢东西、不杀牲畜。“红军”和“干人”打成一片,他们帮着大家扫院子、挑水、修篱笆、做农活。“红军”将地契分给了村里的“干人”,“干人”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田地,而我家的米坛第一次装满了杂粮。
那天,我从山上砍柴回家,娘告诉我,已经有人替她看过病了,是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
我走进灶房,看到灶沿上放着几袋油纸包好的草药,旁边是一只土碗,边上搁着一枚铜子。
“那兵伢子说,井是老百姓出力挖的,开水是老百姓用柴火烧的,柴火也要花钱买,喝水不付钱是绝对不行的。这不,我转个身,他就悄悄把铜子留下,他啥时走的我都不知道。”
“娘,这支队伍真不赖。”
“是呀,他向着咱们干人呢。”
几付草药下去,娘的身子渐渐好转。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给娘看病的那个“兵伢子”不简单,他一家家的把脉问诊,那些得“鸡窝寒”的乡亲喝下他开的药,竟渐渐恢复过来。村子里到处流传着“红军医神,药到病除”的说法。可是,我却一直没能正面看到那个“兵伢子”。好几次,只是看到他背着药箱的背影,一闪而过,就进了别家院子。我一个大姑娘家,虽然对这个有本事的“兵伢子”很好奇,想着亲眼看看他治病救人的手段,却又不好跟进去。远远看着,瘦瘦高高,很年轻。
那终究没有对上一面的小红军,我却感觉那么熟识。后来,这个小红军就长眠在高高的红军山上,每到清明,我都会在坟前烧上一炷香,一烧就是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