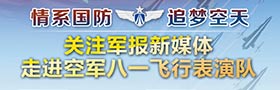军医讲述:探求当代军医价值
讲述者为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军医,47岁,曾多次参加国家层面的非战争军事行动。
我的家乡在遵义。附近“红军山”上有一座烈士陵园。小学的时候,每逢清明节,老师都会领着我们去那里拜祭。我发现,在“红军坟”旁的“女红军卫生员”铜像前,红绸缠绕,香火鼎盛,与寂寥庄严的陵园形成反差。
她是谁?老师和爸爸给了我两种答案。老师说,这里埋葬的是一位被国民党杀害的女红军,被群众赞誉为红军的“神医”。爸爸说,铜像塑错了,应该被拜祭的,其实是村子里一位长辈的救命恩人。他的确是红军,但他是个男的。多大年纪?什么长相?不知道,因为那会儿爸爸还没出世,亲历者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铜像的故事,是我儿时一个深刻的记忆。或许,“了不起的红军卫生员”是我日后选择从军从医的一条重要原因。
一次,看着铜像前牵线般顶礼膜拜的人,石碑上栓满的红布、红绸带和青烟袅绕的香烛,13岁的儿子对我说:“爸爸,看,那些人在烈士墓前搞迷信!”我呆了一下,是呀,所谓“红军菩萨”,当然是“虚构”。还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老师就告诉过同学,三四十年代,红军或者八路军卫生员会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西药混在草药里给老百姓治病,对从没用过西药的穷人来说,肯定“药到病除”,所以才越传越神,以至于被当作神明顶礼膜拜,这尊铜像也许就是这样。可无论事实真相如何,一到清明,铜像前那柱香要是不上,当地老百姓心头就过不去。于是,我扭过头对儿子说:“孩子,这不能算是迷信,这是一份情哪!”
多少年来,我也一直行走在探求当代军医价值的路上。
那场举世震惊的8.0级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作为众多医疗队员中的一个,我曾奔走战斗在抗震救灾的现场——
我和战友顾不上片刻休整,立即分组,逐个察看伤情,快速分检,紧急手术,在最初的24小时内,就完成救命手术上百例。伤员一批接着一批,手术一台连着一台。48小时过去了,72小时过去了……我疲惫地擦汗,回头,却分明看见身后那躺在担架上的姑娘,正悄悄拭去眼泪。
在可怕的埃博拉病毒肆虐西非之际,作为中国首批援利医疗队队员,我和战友在国家和军队召唤“点到”之时,每一个“到”都回答得干脆响亮——
60多天,“敌人”远不止埃博拉病毒,还有闷热潮湿、缺水少电、蚊虫蛇蝎……在困难面前没有一个人退缩,高调向“敌人”宣战。我们以笑脸相互鼓励、支持,也在用笑脸告诉当地民众,为了那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我们时刻准备冲锋陷阵。
我不知道,“红军坟”和“红医”故事将来会不会被某种形式所记录,但可以肯定,从红军时代传承的血脉与精神,一直在时代变迁中延续。或许,这就是“红军菩萨”的终极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