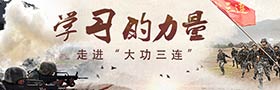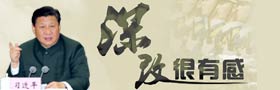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与名院名校毕业留在大医院的年轻医生不同的是,秦叔逵是灌木丛中长出的大树,无名“小”医院里出来的大专家。
1990年秦叔逵调入解放军八一医院肿瘤中心时,这里常常被戏称为“八字没有一撇”的小医院小科室。
“单位小、没名气,我们更要加倍努力。”1992年,秦叔逵通过“打擂台”,以原全军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第二年初即临危受命,从普通医生被直接提拔任命为肿瘤内科主任,时年35岁。
人生的高度,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自己本人的志向、胸怀和格局。
秦叔逵一接任主任,就决定主攻消化系统肿瘤,尤其是肝癌,制订了科室发展的“三个三年,九年计划”。科室三年一个台阶,从江苏省走向全国,再迈出国门,向国际进军。这些目标都一一以实现。
然而,对于自己的个人成长,这个科室几乎是贫瘠的土地,必须走出去,请进来,才可以吸收营养成长。
1992年5月,秦叔逵跟随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孙燕、上海胸科医院的廖美琳、广东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管忠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张嘉庆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的李龙芸教授等老前辈一行六人,第一次组团去美国,参加全球最顶级的ASCO学术年会。
会议期间,不断有各国的代表问道“你们是日本医生吗?”,我们要不断地加以纠正“不,我们来自中国”。会上,欧美和日本学者报告了许多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成果,而中国医生只能坐在台下听,因为拿不出任何研究来,差距十分巨大。
从美国回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秦叔逵都在深刻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实现零的突破。
1992年-1998年,他每年都利用参加ASCO年会的机会,去美国不同的国家癌症中心参观、学习3个月。1999年,他又作为军队公派高级访问学者到美国MDAnderson癌症中心工作学习了近一年,主要是学习如何开展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包括试验的设计、程序、质量控制和总结等等。
这样的学习,不仅让他迅速接轨了国际最前沿的思维和理念,也让自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停下来回看自己走过的路,这对于擅长全面布局的人十分重要。
上世纪90年代,国际肿瘤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彼此间的协作越来越融合,而中国的肿瘤界却因历史原因依然各自为政,工作、学术和政治关系搅和在一起,极不团结,严重影响学术发展。
秦叔逵等一批年轻学者很想改变这样的局面,想团结起来搞学术、搞协作、搞研究。年轻人的想法得到德高望众的吴孟超院士、廖美琳和孙燕教授等的强有力支持。
1997年1月,在北京龙潭饭店举行了一次小型的筹备会,参加人员不到20人,除了吴孟超院士、孙燕和廖美琳教授等,主要是中青年的核心成员,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储大同、王金万、南京的秦叔逵、哈尔滨的马军、湖北的于丁、广东的吴一龙、上海的王杰军、山东的宋恕平、安徽的刘爱国和大连的王怀瑾等。
同年4月30日,以200多名中青年医生为主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中心(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的前身),作为二级学会正式成立了,吴孟超院士担任名誉主任委员,孙燕和廖美琳分别担任指导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储大同教授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叔逵教授担任秘书长持续了12年,直到2009年后的4年,担任学会的主任委员。
CSCO一成立,年轻肿瘤医生的活力急速迸发,推动着中国的临床肿瘤研究快速与国际接轨,用循证医学和多中心研究的思维,中国的肿瘤诊治水平快速提高。7年后,CSCO年会的参会人数超过万人,到2015年,CSCO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肿瘤学术组织。
秦叔逵教授很推崇一句名言“不谋全局,则不足以谋一役;不谋万世,则不足以谋一时。”他说:“个人的职业生涯和学科的发展进步,都必须有一个全局观和目光长远。”
临床医生迈出的每一小步,都是患者生命走出的一大步。
15年前,对于晚期肝癌,临床上几乎束手无策,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只能采取支持对症治疗,病人的生活质量很差,生存期很短。这对于肿瘤医生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和难关,也蕴存着机会,临床需求巨大而迫切,秦叔逵决定以此作为科室和个人的主攻方向。
肝癌是全世界常见的恶性肿瘤,但是由于发病原因不同,各国肝癌的异质性很强,尤其是在亚洲和中国,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疗方案,对于中国患者并不完全适用。
秦叔逵必须为中国的患者闯出一条路来。
虽然是西医,但从小就受到祖国医学的熏陶,他对中医药很感兴趣,希望从中获得突破。“以毒攻毒”是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一个重要法则,即以药物的毒性来攻克癌毒,他与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合作,开展“有毒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包括砒霜、莪术、蟾蜍以及藤黄酸制剂等一系列研究,希望采用现代化的思维和手段研究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自古以来,砒霜被认为是巨毒之药,武大郎就是潘金莲用砒霜毒死的。在中国很早就被用于治疗白血病,曾经是血液肿瘤医生秦叔逵就用过。他向马军教授请教,想移植到肝癌上试试。马军教授,现为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1982年从国外回来后就一直在这方面做深入研究。
1997年,秦叔逵教授把砒霜先在小白鼠身上试用,1999年开始用于人体,做了30多例,效果很好。为此,孙燕院士牵头做了全国多中心研究,把秦叔逵的单中心研究结果重复出来了。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正式批准砒霜增加了晚期肝癌这个适应症。
“在当年没有任何有效药物的时候,它是一个不错的药物。”秦叔逵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把砒霜制剂静脉注射到人体的情景,“真是很害怕出事情,头两天我都是亲自在床边盯着静滴,确保病人的安全。”他说,结果一个疗程以后,病人的疼痛就消失了,两个疗程以后,达到PR(肿瘤缩小了一半),第一例患者存活了5年多。
如今,砒霜成为我国肝癌一线治疗用药的三种方案之一。但是,由于该药物的特殊性,直到现在,医生使用都需要特别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