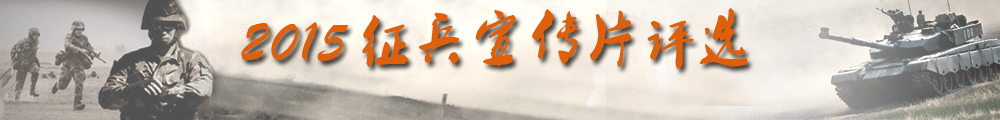唱给番薯的歌
作者:吴永川

文章摘自吴永川编著的《榕叶集》
一次宴席上,端到面前彩绘描金的餐盘里,是一个很考究的银色锡箔纸小四方包。剥开微微发烫的锡箔,竟是一小块精心烤制的红薯。我心一动,番薯,什么时候你身价陡增,登上这华贵的宝座?
筷子夹着红薯,我的心却展翅飞过千山万岭。我仿佛又看到那铺满故乡大地绿油油的番薯园,仿佛又见到母亲戴着尖顶斗笠,汗水湿透衣衫后背,在番薯地里耕作的姿影。她在番薯地里劳作几十年,是她和番薯一起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
传说番薯原产南美洲,明朝辗转传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所以,老家闽南,称红薯为番薯。它是家乡种植最多的一种植物,不需太肥沃的土地,不需太多的水,培育简便,产量又高。村子里除了不多的一些水田栽水稻,旱地、山坡种的尽是番薯。村里人常说:“番薯非常贱,一点也不娇贵,好种好活。”
开春,母亲借来耕牛和犁,把家里那几块瘠薄的沙地犁成一垄垄的。买来薯苗,间隔均匀地插进垄里。没过几日,番薯苗生根发了新嫩叶。一条条番薯苗像藤一样,贴着地面四处蔓延。给番薯施肥,得把薯藤翻到垄的一边。施肥后再翻回来。母亲常让我们帮她“翻藤”。母亲翻得快,碧绿的条条薯藤在她胸前飞舞似的。不用多久,密密匝匝、幽幽绿绿的番薯叶,盖得见不到一点泥土。没有蔬菜吃,有时就去摘些番薯叶,炒熟后有股野菜的清香。夏季,是番薯茂生的季节,从村后清源山脚到村前,碧绿的、漫漫无边的蕃薯地一直铺张开去。除了小河和几口池塘,一片碧绿。大地充溢着生机,让人心醉。清晨,迎着金黄的阳光,露珠在碧玉般的番薯叶上闪亮,放眼望去胜过五彩锦缎。那时节,你躺进两垄番薯之间的番薯沟,浓密的绿叶可以把你遮盖得严严实实。解放前夕,村里的小学校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中心。那天,城里国民党军队来搜查。一位地下党员的小学老师得到风声,飞快钻进学校前的番薯沟,快速匍匐前进,安全转移到邻近村里去。家乡的番薯园,像北方的青纱帐,对革命还有过贡献呢!
番薯的块根不动声色地在泥土里生长,从不露脸张扬,不像石榴,开花结果都很扎眼。秋天,母亲翻开密密匝匝的薯藤,见根部泥土有裂缝,便晓得地下已有成熟的番薯。这时,母亲挎着小竹篮,用铁制“番薯铲”轻轻拨开泥土,摘下硕大的番薯,然后再把土盖好。还未成熟的番薯,继续在地里长大。最早挖出的番薯,家里是舍不得吃的。挑着卖给城里人尝鲜,能卖上好价钱,只有到了番薯大量成熟,我们才开始吃上新鲜的番薯。深秋初冬,番薯叶一天天枯黄,土里的番薯不再长大了。母亲领着我们拔掉所有的番薯藤。薯藤有的切碎熬熟作饲料喂猪,有的晒干作燃料。听小妹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稻谷、番薯都歉收,母亲和她连枯干的薯叶都拿来充饥。
在拔去薯藤的地里,母亲用借来的耕牛和犁,犁开一条条番薯垄。成熟的番薯,随着犁铧从土里跃出来,左蹦右跳。 我们跟随在犁后,手脚不停地把番薯捡到竹篮里。收获的喜悦,让人心头发颤。家里那只小白狗,也摇着尾巴,跟在耕牛屁股后奔来跑去。那些日子,房前屋后满眼的番薯,屋里墙边地下堆的尽是番薯。番薯的品种也多,有红皮红心,有紫皮白心, 有白皮白心……母亲让我们按照品种、大小,分门别类堆放。番薯容易霉烂,一年主食又靠它,村里人全忙着在加工番薯干。母亲白天地里忙活,只有到了夜晚,点上煤油灯,用刀把番薯切成片切成条,或用钉在木椅上的刨刀刨成片刨成条。油灯火太小,一次母亲不小心,让刨刀擦伤手指,血流如注。唯恐番薯烂掉,她拿香灰止血,用破布包扎, 又继续刨开了。那期间,家家屋顶上、晒谷场上,晒的是清一色的番薯干。在村口,就能望见座座屋顶一片银白,就像北方冬天的积雪。进入村里,简直是番薯的海洋。番薯晒得干透,装进陶缸里、木桶里、麻袋里,就是储备粮了。有一种番薯,可以生着贮藏过冬,蒸熟后又格外甜软,不过,产量不太高。许多农家每年都在收打稻谷的大木桶里贮藏这种红薯,桶的周围撒上石灰,防潮防鼠。在春节贴春联时,大木桶上贴着艳红的“五谷丰登”。经过包装的番薯,简直被奉为尊贵宾客。此时此景,让人感到番薯似乎有了自己的地位。
从初秋番薯下地以后,家里一日三餐“番薯糊”。配糊吃的,也千篇一律,是母亲腌制的咸菜和酱瓜。每日,天微微亮,全家人还在睡梦中,灶间(厨房)里就传来“嘶啦、嘶啦”的响声。母亲早早起来“磨糊”了。她用铁钉打满眼的铁皮,把番薯磨得细细的,像浆糊一般。为了拿到番薯的淀粉,在一个大陶缸上,隔着竹编的篓和抹布,用水一遍遍地淘洗番薯糊。缸里的水沉淀半天,倒去上面的水,缸底就积下厚厚一层白花花的番薯粉。这是番薯的精华,家里却是舍不得吃,晒干后卖到城里去,好买油盐、布料。城里人用它做粉丝、粉条。那都是高级食物,家里难得一见。
经过滤去部分淀粉的番薯渣,倒进大鼎(大锅)里,掺水煮熟后,便是一家的三顿饭。有时,年景好,稻子丰收,番薯糊里添进少得可怜的白米。白米粒在大鼎里,寥若晨星。母亲的娘家惠安,水田少,大米更少见。那里有句形容的话,叫“惠安鸡——见米会反弹”。可见母亲从小生活的凄苦。我们兄弟姐妹哪个生了病,母亲用小纱布袋装点大米,扎好放进“番薯糊”里一起煮熟。解开布袋倒出一碗白米饭,就是特殊的“病号饭”。一大鼎番薯糊吃三顿,恐怕发馊,中午在灶里添几把火加热。有时,番薯糊发馊发酸,母亲仍不舍得喂猪,自己喝上两大碗,而给我们重新做番薯稀饭。我进城上中学,午餐自带大米,学校卖给每人一个陶罐,绑上写着各人姓名的竹牌,校工帮助添水蒸熟。我们这些农家子弟的饭罐里,都不会是净白米饭,总要塞进一两块番薯。家里过节日时,难得煮顿米饭,也要掺进许多生的或干的番薯丝。一日三顿,没有哪顿缺得了番薯。生番薯吃光了,便开始吃储藏的番薯干。一年四季,没有哪天离得开番薯。这种生活实在单调,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母亲常说:“吃鱼会腻,吃肉会腻,吃番薯不会腻。”有的人家地多,还用番薯酿酒。可是,喝酒的人都轻蔑地叫它“番薯酒”。不知是酒劲不足,或者不如米酒价钱高,或是就因为它是番薯酿造的?
上中学后,看书当中,常见诗人歌吟稻海、麦浪,番薯却得不到他们的青睐。相反,番薯常常招来人们的白眼。闽南人普通话说不好,方言味浓,被人嘲笑为“一口番薯腔”。村里人揶揄谁干活笨,挖苦哪个人傻瓜,一句话:“番薯料!”母亲感叹自己命苦,常说:“咱命歹,谁叫咱生的番薯命!”父母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书,说的也是:“不好好读书,没什么出息,就是一辈子番薯命!”那时候,对番薯,家乡人就是这般既离不开它,又无可奈何地抱怨它。
离家多年,我仍无法忘情于故乡的番薯,就像母亲说的:“番薯几日不吃就叫人‘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我不时在心里为番薯的地位抱不平。番薯,要求人们的那样少,而它从根藤到叶,全身都奉献给了人们。可是,对它却那么轻视,实在太不公平了。番薯,的确是“贱”,那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它的确不稀罕,随处可见,要不怎能养活那么多穷苦人的生命。难道因为产量高数量多,就可以淹没它的价值,就该落得这么低的待遇?我常常想,真应该为番薯唱一支颂歌。
难忘啊,故乡的番薯,养育我成人的番薯!
(2001年10月30日)
文章摘自吴永川编著的《榕叶集》
作者简介
吴永川,1939年7月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清源山下花园头村,就读环山小学、西隅中学、泉州一中。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62年至1999年在解放军报社工作,历任编辑、副社长、副处长、总编室主任。曾任首届全军新闻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90年至1999年历任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政治委员。教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