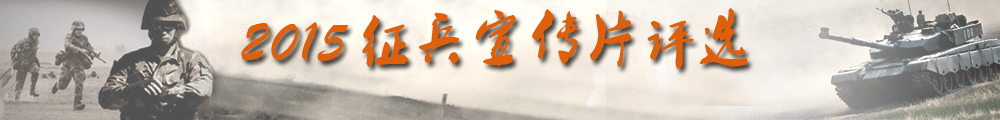又是一年毕业季,大四的学长们在一纸调令到来后背起背囊奔赴祖国的大江南北。看着调令上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名,忽然阿里这个略显熟悉的名字突兀的挤进了我的视线。细细的搜索着自己的记忆,我终于把这本正在我脑海深处某个角落里慢慢发霉的书翻了出来--《当兵走阿里》,一本记载了高原官兵音容笑貌的书。
翻开书的第一页,以雪山为背景的纸上印着一排有一排名字:2011年3月11日,驻阿里某部主任耿显峰归队途中遭遇车祸牺牲,23岁;2012年8月22日,陕西省援藏干部张宁,不幸心脏病突发死亡,44岁……这一个又一个牺牲的军人,大的44岁,年轻的只有20岁。他们的生命都永远的随着雪山上的冰雪凝固在了阿里这片圣洁而又严酷的土地上。医学上把海拔超过3000米的地方称为高原,而把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区称为"生命的禁区",因为这里不适合任何生命的存在,而阿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死亡在我们眼中似乎是一个很陌生很遥远的字眼,但在这里却是一个极为稀松平常的词汇。带来死亡的可能是那千山万壑中的一次车祸,可能是一次灾害意外,可能是突如其来的高原反应,甚至可能是毫无征兆的突然猝死,死亡距离驻守在这里的高原官兵是如此之近。自从国境线从这里划过的那一刻起,戍边的历史,就是由鲜血和生命浇筑而成。跟随着作者的足迹行走在天界,和她一起体会着神仙湾的恍惚,搓板路的颠簸,还有死人沟的阴森,一路走来,才能体会什么叫与死亡同行。然而真正的震撼,却来自于喀喇昆仑山口的那个触目惊心的颅骨界桩,他静静的矗立在茫茫雪原上,仿佛在向我诉说着那一个又一个定格在雪域高原上的鲜活生命的故事。
忘不了,高原战士暗红色的高原脸;忘不了,战士们咧嘴一笑时从干裂的嘴唇上汩汩而出的紫黑色鲜血;更忘不了,作者那只承载着牵挂、亲情和伤痛的红色帆布旅行箱。每当这个红色的旅行箱出现的时候,便代表这又一次的分别。边防军人的职业注定了他们与家人的聚少离多。一次又一次的分别使他们在父母眼中的形象逐渐化为那一道渐行渐远的背影,在孩子心中的印象也最终变为那一抹军装绿和那个代表着别离的旅行箱。看到作者笔下那个见到男军人就叫爸爸,看到女军人就叫妈妈,独自一人在深夜无助的哭泣的孩子,行李箱上本应代表温暖的红色在那一瞬间变得如同鲜血一般冰冷刺目。大都市之中那些娇贵的能彰显身份的名贵箱包无法随着卡车在高原的乱石上颠簸,是一个个皮实的军用旅行箱在高原上不停的摔打、拖行才换来了那些名贵箱包在城市中安然前行的机会。在祖国光鲜亮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能在世界人民面前挺直了腰杆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有那么一群人在用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奉献着。戍守边疆,保家卫国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信仰,一种深深根植于他们灵魂深处的信念。如若山河破碎风飘絮,又要有多少人身世沉浮雨打萍?
边防的历史,是用军人的血肉书写的,一代又一代边防军人用他们的生命谱写出一篇无言的史诗,看看康西瓦烈士陵园里一排又一排烈士的墓碑整齐的排列在荒芜的土地上,如同他们生前等待检阅时一样庄严肃穆。灰色的石板上刻着烈士的名字,让人看一眼就不禁心生敬意。但是更多的墓碑上却仅仅用苍白的笔触写着"无名氏"三个字。这是真正的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烈士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挥了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甚至连一个可供人回忆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只有一个灰突突的墓碑默默的矗立在这里,提醒着人们有一位忠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这里长眠。他们留在了这里,留在了他们付出汗水、付出鲜血,并最终付出生命的地方。